《昨日世界》:沉默的教養與文明的回聲
最近台灣的社群媒體(文章完成時)又開始熱烈討論起「台灣文學」的定義,圍繞著語言的歸屬、風格的正統以及文學主體的界定所展開的討論,背後其實透露出一種深層的焦慮,也就是對於自身身份認同的困惑與不安,而這種對文化身份的焦慮,讓我不禁聯想到茨威格的《昨日世界》。
茨威格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歐洲人」而非使用德文的奧地利人或是奧地利的猶太人,他筆下所描述的維也納文化與德國文化之間存在著微妙卻明顯的差異,透過他的文字,我們也得以重新審視所謂身份認同的複雜性。
消逝的黃金年代
茨威格回憶起他童年時代的維也納,那時的歐洲文明正處於黃金時代的尾聲,人們雖然尚未對未來產生明顯的恐懼,也沒有明顯的焦慮,但這種安靜與有序的日常,充滿了對文化與藝術細緻的品味,宛如一條輕柔的河流平靜地流動,似乎能夠永恆地延續下去。
但這樣的安寧實際上更像是暴風雨來臨前的短暫寧靜,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原本堅實的文化秩序瞬間遭到戰爭的摧毀與瓦解。
茨威格自己坦承,他原本並沒有撰寫自傳的想法,也不認為自己的生命需要被記錄,他一直覺得真正有價值的經驗應該被轉化成小說、戲劇或思想的形式,而不是直接裸露地記錄生活細節。然而,經歷過兩次戰爭與極權主義如洪水般席捲而來,將他所堅信的自由、文明與人道價值徹底撕碎時,才不得不放下內心的抗拒與矜持。
他認為,這樣的書寫並非出於自願,而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
因此,《昨日世界》與其說是一位名作家的私密告白,不如說是一份文明的見證;是一個信仰秩序與理性的知識分子,在世界即將崩解時仍試圖留下話語的努力。這本書並非用來發洩情緒的筆記,也不是高高在上的歷史總結,而是一種近乎羞怯卻堅定的言語姿態:我依然相信,因此我無法沉默。
他並沒有在控訴什麼具體的事情,而是更希望未來的讀者能夠看見,曾經有這樣一個世界真實地存在過。這裡也讓我想起赫曼・赫塞曾說,他希望五十年後仍有人閱讀他的文字,那是一種對未來的信任,也是對書寫的謙遜期待。
緩慢而堅定的聲音
茨威格的文字節奏緩慢而有一種音樂般的呼吸節奏,放在今天這個追求快速、直接且充滿表態需求的時代,他的語氣顯得異常突兀。他不急於為自己辯護,也不急於表達立場,他寫作就像是一種自然的呼吸。
茨威格關注的是戰爭發生之前的世界。他試圖探討人們如何思考,如何在不必選邊站的情境下學習對話,如何讓教育、語言與文化變成一種自然的日常氣質。
他描寫十九世紀末的維也納,那時的孩子學習拉丁文、希臘文,家庭中有鋼琴、有豐富的藏書,對藝術有著自然的尊敬。這樣的情境並非單純的文化堆砌,而是一種無需即時回報的精神投資,這種投資並非出於功利的計算,而是為了形塑一個完整的人格。
溫柔的批判者
在書中,茨威格批評學校教育如何壓制創造力,如何以紀律取代個體的自由與個性。他並非訴諸理論或口號式的控訴,而是以非常私人的方式表達,讓讀者能夠感受到一種不自覺地被剝奪的失落感,指出從小被訓練成服從與沉默的教育,才是真正令人憂心的地方。
茨威格的批判風格十分溫柔,他並不製造對立,也不設定敵人,在他的敘述裡沒有勝利者,只有記錄者。他描述維也納人如何對意識形態保持冷感,在公共場合如何維持適當的距離與禮貌,這種態度在當今人人急於表明立場與價值觀的時代,幾乎成了一種過時的美德。但也正因如此,才更清楚地讓我們意識到自己早已習慣了爭奪與對抗。
精神日常的記憶
《昨日的世界》所描繪的並非一個完美的世界,它充滿階級問題、侷限與特權。但在這個框架下,茨威格依舊捕捉了人與人之間自然的互動節奏,對知識的熱愛並非來自焦慮,而是來自信任與從容。這樣的精神日常,並非象牙塔式的幻想,而是實際存在過的文化景觀。
茨威格的人生正是這個世界的縮影,從維也納的文化黃金時代出發,到經歷戰爭、流亡、國籍喪失、朋友死於集中營,最後在巴西結束自己的生命。他撰寫此書時早已意識到過去無法重現,然而他仍執著地說:「我還記得它,我不願它白白消失。」
今天閱讀這本書,也許無法從中找到明確的答案或立場,但能學到的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一種不急躁、不焦慮、不急於表態的語氣。這樣的語氣提供了聆聽與沉思的空間,在這個一切都需要表態的時代,語言同樣可以是一種安靜而堅定的力量。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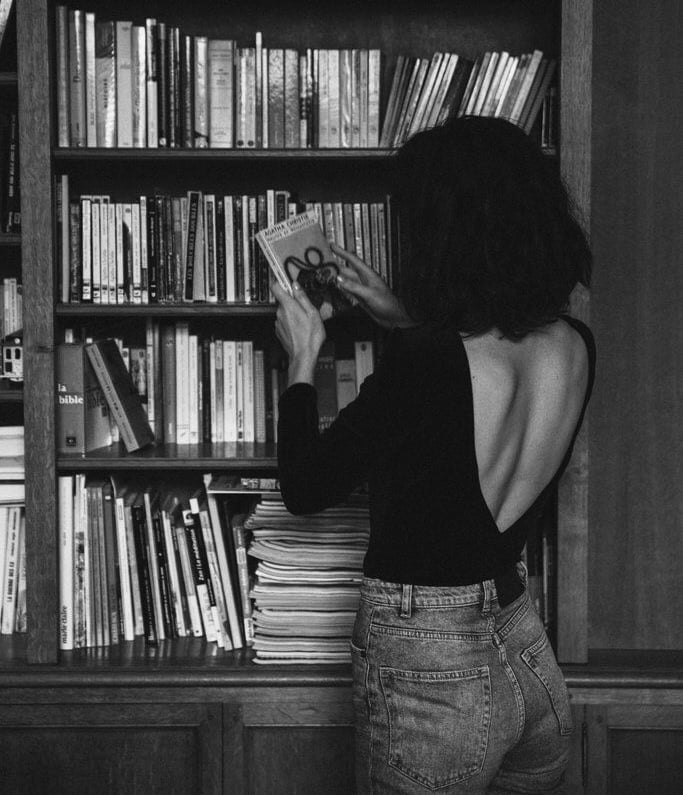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