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的幻滅
這篇文章我會一氣呵成的寫下,只是想記錄自己腦中的運作是否還正常,可能會花半小時寫下片段式的想法,當作是一種頭腦復健。
去年春天,我去了一趟巴黎;年底又去了羅馬和佛羅倫斯,並從佛羅倫斯搭廉價航空飛了巴黎,當時我把行李寄放在凡蒂岡的公寓一週,屋主沒和我抽取任何費用,說因為覺得我是很有禮貌的租客,她的行為也挽回了我對於羅馬人的偏見。
我對羅馬人的偏見,是我認為他們比較排擠像我這樣的外地人,當然也包括我並不會說義大利人,而且我一直認為要偽裝成法國人比義大利人更加容易。也許是法國人引以為傲的自由,對外地人而言更加能融入。
每次去巴黎,若是從外地搭火車,我總想像一兩百年前的歐洲人或東方人進入巴黎的期待,也會想像自己像巴爾札克筆下的外省人,我想像自己有點天真老土,因為我還有一個很真實的性格,卻逐漸被巴黎的虛偽、人情冷暖與金錢社會的規則吞沒。
實際的我,其實更適合居住在都市,但我厭惡偽裝的程度嚴重到無法接受任豪意義上的意識形態,不論是褒或貶義。
外省人的才華,在巴黎並不算什麼,然後是媒體輿論操控著文學走向,因為他之後會找到一條在巴黎生存的方式,那樣的現實感讓我很害怕,因為我之前預期的事情也一一出現。當你能預估到壞事時,你並不會對自己的預言能力感到自豪。
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有才華,甚至有一個很老派的靈魂,堅信自己從以前到現在經營在文字路上的路程是必要的,我的老派讓我不能接受社會中的急功近利。那時的報社為了吸引讀者眼球,不惜捏造事實、渲染情緒,評論與新聞之間沒有界線,真相與謊言也早已混淆。寫手們的筆桿不再為正義或真理服務,而是為金錢、報酬與曝光而動。
他揭露了報業如何從理想性的「第四權」墮落為金錢與權力交易的工具,記者不再是秉持真理的筆者,而是可以被收買、被操控、甚至反覆立場的人。
呂西安原本懷抱文學理想,進入報界後卻逐漸學會如何操縱讀者情緒——一個人能掌握文字是蠻可怕的,我之前在《那不勒斯故事》中的評論有寫到——,甚至以惡意評論毀掉他人的名譽,為的是賺取稿費、贏得版面、換取上流社交圈的關注。
《幻滅》中近乎預言性的筆觸,描寫了一個輿論如何被收編、被商品化的社會。巴黎報界,反映的正是現代媒體結構的雛形,挖掘真相或創造故事的拉鋸一直在進行,在聲音洪流中,真相也容易被犧牲。
在二十世紀初旅行巴黎的茨威格則有不一樣的想法。近一個世紀後,造訪巴黎的茨威格,看見了另一種風景。在《昨日世界》中,他筆下的巴黎是一座「世界精神的首都」,是自由與思想開放的象徵。他讚嘆那裡的報刊、文學沙龍與知識人所激盪出的文化氣息,即使戰爭的陰影漸近,巴黎依然像是一場未醒的夢。
對巴爾札克而言,巴黎是夢碎之地;對茨威格而言,巴黎仍是夢的所在。
我認為的自由或許不是絕對的,而是有其社會結構與現實條件的限度。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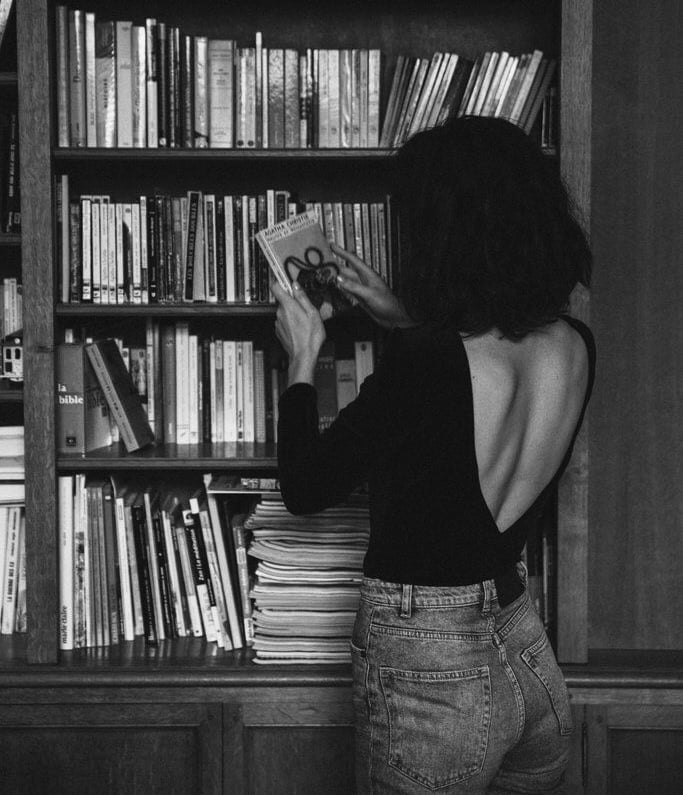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