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身无用”是安卓思维还是苹果思维?
Self-Development Ethics and Politics in China Today第5章
“你得有核心肌肉”:白领女性1中的锻炼与身体/自我规训 “You’ve Got to Have Core Muscles”: Duanlian (Exercise) and the Disciplining of the Body and Self among White-collar Women
彭馨妍 Xinyan Peng
摘要:通过在上海开展的人类学田野,我遇到的职业女性将自身身体视为付出辛勤劳动、体现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的重要场域,并将“锻炼”(duanlian)作为一种正当方式,用以培养并将工作伦理延伸至工作场所之外。本文把“核心肌肉”的社会性价值与当下都市中国职业女性中盛行的、与自我发展相关的“全都要”话语联系起来,正是这种话语塑造了她们在工作与身体上的双重用功。当女性训练身体以贴合成功职业主体(健美且高产)的标准时,自我规训、自我发展与辛勤劳动的性情被具身化,并从工作场所转置到家与工作之间的其他社会空间。关键词:锻炼(duanlian)、身体训练、自我规训、自我发展、职业女性、“全都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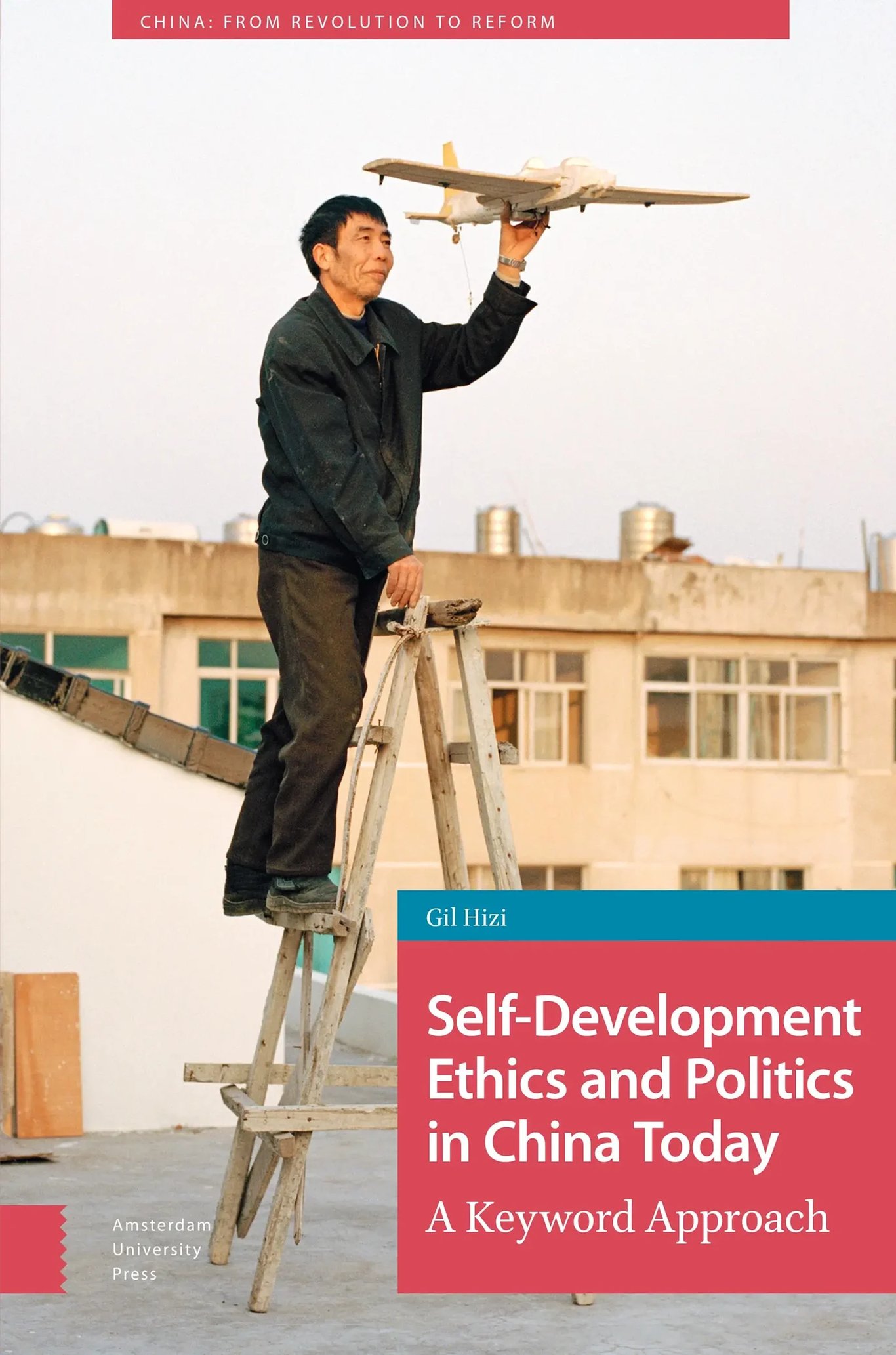
引言
炎夏午后,灼目的阳光透过窗户,办公室空调几近失效。几个渴望冰沙的女性围在一位同事的手机旁,准备集体下单。“嘿,你也来一杯吗?”热心同事话音未落,老板——一位把自己称作 Jessica2 的女性——走了进来,她先是评价了 Chan 的身材:“我很喜欢你的上衣!你看,你的马甲线都能看见了。[…] 看起来真不错。”马甲线,是流行中文俚语,指的是身体躯干中段稳定性肌肉(即核心区)呈现出类似束身衣形状的理想线条。老板的夸奖把大家的目光都引到了 Chan 的腹部——她特意穿了短款上衣(在职场女性着装中并不常见),让我们能够看到。“太厉害了,你刚给新生儿喂完奶就把核心肌肉恢复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有人钦佩地问。Chan 带着明显的自豪回答:
你知道的,我一生完孩子、断奶后就立刻开始训练身体。[…] 我以前的身材很完美,后来一度走样。我不想和生孩子前的核心肌肉说再见,我非常想把它们找回来。现在它们回来了!
这个开场故事讲述了一位年轻白领女性——一位刚经历过分娩和哺乳的新手妈妈——在办公室自信地展示她的核心肌并收获同事赞美。它表明,马甲线/核心肌肉已成为当下都市中国白领女职工的骄傲之处,并在职场中被热议。Chan 对因分娩与哺乳导致身体变化的描述,以及她为恢复至产前体态所做的努力,揭示了职业女性对身体、尤其是生育之身的焦虑,也揭示了她们为克服生育相关体型变化所带来的不受欢迎的影响、甚至羞耻,而在自身身体上付出的规训性辛勤劳动。未经历生育相关身体变化的女性同样重视体形,并经常进行锻炼(duanlian)。
在我于2017—18年上海进行的人类学田野中,我在办公室与家庭场景中做参与观察的同时,还跟随十余位女性下班后来到一家普拉提工作室,观察她们训练核心肌肉,以及如何在隔间之外具身并延展辛勤工作的伦理与自我发展的话语(Peng 2020)。这些女性规律上课,平日夜间与周末每节课时长一小时至一小时十五分。田野期间,每节课约需80—100元人民币(约合12—15美元),需要通过电话预约。该工作室位于上海市中心附近,常客几乎都在几站地铁内的公司上班,从下班直达不超过30分钟。有些女性平日晚间与周末甚至连续预约两节课,以便在有限的非工作时间里最大化训练量。
本文主要基于我在上海一间普拉提工作室与职场收集的民族志材料,分析精致的核心肌肉如何成为职业主体与奉行自我规训、自我发展和辛勤劳动的女性身体的地位标记。通过考察当代都市中国职业女性的锻炼(duanlian)之社会实践,我指出核心肌肉作为纪律与辛勤工作的可视化指针,其社会性价值与面向职业女性的“全都要”式自我发展话语相互契合。当女性在社会对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要求交叉处为自身身体焦虑之时,锻炼将工作伦理从工作场所转置到其外部空间。面对生育给事业与身体带来的挑战,女性努力工作以捍卫自己的工作权,同时保持身体线条,以回应社会对其生产力与生育力同步提升的期待。换言之,锻炼中所具身的辛勤劳动、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旨在维持职业女性与公共领域的生产性劳动的关联,并使她们与私人领域的再生产性劳动保持距离。本文关注的不仅是生产与再生产交叉处的女性身体,还关注家与工作之间空间中锻炼(duanlian)的社会性。
锻炼、通过身体实行的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
我在上海观察到的白领女性对核心肌肉的迷恋,并非现代中国职妇首次将身体以生产性术语加以表述。社会主义时期,身体与人格以军事化方式被塑造,用以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并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贡献。20世纪50—60年代公共话语强调通过劳动与体育把身体“锻炼”(duanlian)为“百炼成钢”,展示“解放后的身体在工作中的新生活力”,并强化“铁一般的身体”的可欲性(Chen 2003b, 365)。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动员女性进入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公共领域劳动之际(Peng 2022, introduction),模范工人的视觉呈现——特别是进入公共新岗位的女性——构成社会主义身体政治的核心主题。以劳动妇女为特色的宣传材料改变并“硬化”了女性身体(Chen 2003a, 271);强健的女性身体——尤其突出展示肌肉感的手臂与小腿——挑战了职业空间与劳动的传统性别分工,推动社会主义将女性纳入劳动力与公共工作领域(Chen 2003b, 367)。如果说社会主义时期田间地头与工厂里的健壮、肌肉型女性身体礼赞女性进入传统由男性主导的生产领域,那么在改革时代的中国城市,“美女经济”(meinü jingji)则更为盛行(Peng 2022, 第5章)。

顺着这一脉络,本文展示白领女性如何在下班后训练核心肌肉,并在工作场域之外具身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的伦理,以凸显身体与锻炼(duanlian)在规训女性劳动者于工作场所之外继续辛勤工作的作用。在她们的日常锻炼社会实践中,当涉及女性的生活与自我发展时,身体成为表达并协商社会对生产与再生产要求之间张力的场所。
在我进行参与观察的那间工作室的身体训练课程中,参与的女性很少以躺下或短暂离场的方式休息;她们也不会轻易放弃困难体式与动作。即便老师让大家休息,有些人仍在尝试最后一个——往往也是最难的——动作。老师很清楚这些女性是来通过身体吃苦来“锻炼”的,于是毫不犹豫地督促她们把身体压到更紧:要求某个体式多坚持一会儿、某个动作再多做几次。“你们知道你们是在靠努力练出核心肌肉,”老师一边在场中巡看懈怠者,一边坚定地说。“哇,看看你的核心肌肉,真漂亮!大家,再来五次!”当她看到一位短款上衣下露出完美核心线条的“榜样身体”时,就会抬高对全班的要求。在这种以“模范身体”为标尺的情境中,其他女性即便气喘吁吁,也会在带着赞叹的“哎哟!”声中继续训练。
课堂上常要两人一组完成类似这样的练习:A 平躺在垫上,抓住 B 的脚踝,B 的双脚分开踩在 A 的头部两侧。A 要反复把双腿笔直抬起,理论上要靠核心肌肉发力,而 B 则不断把 A 的双腿向下压。我的搭档很热衷指导我如何调动核心,以便把这个动作做到最好:“不要用臀或腰,专注核心,启动它、用它把腿直直抬起。如果用的是核心,你会感觉很好。否则就会很快累,动作也就失去意义。”
当我不足的核心发力让她不满意时,她让我暂停,把手放到我腹部,轻拍以检测腹部是否紧实——那是是否练到位的标志——同时提醒我要让它更努力工作。做到二十五次抬腿后,我已无法再动。尽管我满脸大汗、笑容变形、抓着她脚踝的手越来越紧,这些都在向她传达我已练到精疲力竭的讯息,她仍不见同情,只是催促我继续。作为回报,她也期待我以同样方式帮助她:让我去拍她的核心看看是否充分“启动”,并更用力把她的腿压回垫面。她抓我脚踝的手汗多到不断打滑。我们的汗彼此粘在对方身上;收拾垫子准备离开时,我们交换了心满意足的微笑。由汗水浸润的地板、垫子与彼此的身体共同调和出一室弥漫的、对辛苦锻炼后成就感的共享气息。
女性参与者鲜少以躺下或短暂离场的方式休息;她们也不轻易在难度动作前退缩。即使课程末尾老师示意休息,有些人仍在尝试最后一个、往往最难的动作。更衣室课后对话里,她们会比较各自锻炼时出汗与受苦的程度。“我的内衣都湿透了!”有人一边用毛巾拭汗,一边自豪地对同伴说。她们自若地指着自己的腰、大腿与手臂,强调肌肉酸痛的程度。“我酸得明天恐怕都来不了上课。[…] 其实我明天可能连上班都去不了!”她们略显夸张的疼痛表达彼此呼应,谱成一曲对辛勤劳动、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之具身价值的赞歌。事实上,我总会在次日晚间看到那些“酸得来不了”的人兴致勃勃地现身课堂。
上述锻炼场景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传统中通过具身实践进行的自我发展,它不是以个人主义方式,而是置于与他者的关系之中(Ames 1993, 149)。活生生的身体是社会自我的一维,既与共同体成员交流,也向他们传达意义。在中国古典哲学中,身体通过其礼仪性行动构造世界秩序,重塑个体与共同体;它是中式整体观或自我—他者“共生”修养/发展的内在组成(Ames 1993, 151)。顺着这一思路,Palmer 对气功群体练习的民族志考察指出,“自我修养/修炼”这一术语的问题在于,它遮蔽了师徒之间具身知识的社会性传递过程。虽然在普拉提工作室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师徒关系,锻炼(duanlian)却确实涉及经验更丰富者向经验较少者传授动作与技巧(Palmer 2007)。
在一个闷热潮湿的周日下午,普拉提教室里,一位年轻女性在两堂课间隙帮另一位把髋部打开:她把对方的双腿沿着墙面推成一直线。帮助者用清亮的声音说:“听说老师在课上纠正你时你挺难受的,我想问题可能是你的髋太紧。开髋对你的身体是好的。”除了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人们也会意识到课堂上与课后他人身体的变化,因此她能洞察对方在课上遇到的困难,随后主动伸出援手。帮助者用脚稳住对方靠墙的一字腿,并指导说:“现在,双臂贴耳向上延展,然后慢慢下压上身。”我听到对方咕哝道:“啊,我的腘绳肌疼。”她颤抖的上身缓缓向地面下降。“看吧?你应该更常练,虽然会难受,但会逐渐变好。”帮助者笑着,汗珠淅沥。“谢谢你。”对方轻声说,并擦拭仍在颤动的上身汗水。
普拉提工作室里,常可见互不相熟的老成员之间的互助。我常见到经验更丰富的女性帮助经验不足者,教她们“吃苦”、甚至“吃痛”的价值。一次课前,我听到两位女性分享如何把某些高难动作做“对”的经验;随后她们彼此帮助在墙边做倒立,双脚抵着镜面。一位女性起初还舍不得离开垫上的舒适位,另一位就不断鼓励她:“来吧!没你想的那么难!你应该试试,挑战一下自己!”随后她们轮流纠正对方的倒立,用手把对方的双腿推到与地面完全垂直,或把对方脚压在镜面。“我说得没错吧?并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你快成功了。[…] 就是要多练。”帮助者对那位努力在无任何支撑下让颤抖的双腿直立的同伴说。这两位女性互不知彼此姓名、家庭或工作,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彼此触碰身体以提供帮助。
尽管彼此不熟悉对方的个人、家庭或工作生活,普拉提课上的女性参与者却乐于在对方沉溺“罪恶小乐趣”后彼此规劝,告知何时、如何吃与练,帮助纠正体态与动作,并鼓励对方忍受贯穿每一分钟锻炼(duanlian)的酸与苦。这些共同体式的“身体苦工”,反过来确认了核心肌肉的社会共享价值:在她们眼中,核心不仅塑形美体,也实证了一位自我规训、自我调节、勤奋用功的个体。换言之,对她们来说,锻炼(duanlian)是一种具身的自我发展。个人训练身体、规整心念的同时,这些又是社会实践:身体技术(如某个动作如何启动核心)与诠释框架(如核心的象征价值)在社会网络中流通并被强化。
当女性尝试共同规训自我与他者时,一种社会性也随之形成;在此语境下,锻炼传达出一种社会化的、具身的自我发展实践。关于身体的古典中国观点把它扎根在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环境相互关联所构成的社会世界中。这些人际联结通过个人身体与外界之间流动的“物质”来具身(Brownell 1995, 241–43)。在女性的锻炼中流动于其间的最重要“体液”是汗:它弥散在训练空间,也粘附于彼此身体。受训之身体并非完完全全属于个人,而是受到搭档的“汗水同伴”规训与推动身体更努力工作的集体压力的支配。在彼此陪伴与规劝之下,女性的锻炼既练就了具身自我规训的核心肌肉,也塑造了“辛勤身体”的社会性,这构成了自我发展的基础。
我已描述了年轻女性在锻炼中承受的出汗、酸痛与受苦,她们并不以自怜加以诠释。Miller 在其关于日本美容产业的研究中质疑一个常见假设:女性为了变美愿意受苦,并在服从美的规范时自我从属。这个假设遮蔽了“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欲望如何参与女性身体的性化与商品化”(Miller 2006, 6)。然而,这一路女性主义批评高度倚赖压迫者(男性)/被压迫者(女性)的二分,将女性定位为在迎合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欲望时“不自知且无力”(Bordo 1999)。Miller 摒弃这种二元模型,洞见地指出,日本女性对美容产业的投入源自“一种社会认可的自我改善”(self-improvement),它与日本关于身体与自我规训/自我发展的长久观念高度契合(Miller 2006, 10)。例如,节食虽与美的理想相关,却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在实践中奖掖与奋斗、坚持、纪律有关的传统自我发展观(Miller 2006, 160)。类似地,或许有人会猜测,我在上海的对话者——白领、职业女性——追求核心是否只是为了“瘦”,而她们通过锻炼(duanlian)辛勤追逐核心是否只是为了变“薄”。我的观点是:她们看重锻炼,在于辛勤与自我规训可以被可视化地索引并通过“体适能/健身”的追求而具身化,这最终对应到与自我发展话语相连的“生产性”感。
富有生产性的辛勤身体与职业女性的自我发展
我在上海工作了几个月的那家营销服务公司,食堂楼下就有一个健身房,四面是大大的透明玻璃窗。我们常常一边吃午饭,一边看着那些抓紧午休时间锻炼的同事:跑步机上奔跑、举重、骑行。办公室里同事常感叹:如果花太多时间坐在工位、太少时间锻炼,体形会很快走样。像下面这样的对话在午餐时常见:
“某某每天早上六点去跑步,不管昨晚下班多晚……”
“哇!我佩服她的坚持!”
“某某现在比以前胖了。她以前每天都去健身,但停了之后体重就反弹了。”
“我们得锻炼,否则每天在办公室坐这么久,身材真会走形。”
这类“身体话语”凸显了对自我发展至关重要的纪律、辛勤与毅力(Brownell 1995),也使一个以通过锻炼(duanlian)保持“体适能/健身”为念的白领女性共同体的身体工作标准浮出水面。与 Cederström 与 Spicer(2015)所称“健康综合征”(wellness syndrome)中的“健康/健身”类似,我在上海接触的白领中,“健身”成为一种道德号令,她们通过言语与实践不断、孜孜不倦地提醒自己与彼此。作为白领所持守的一种意识形态,健身提供“一整套观念与信念,人们可能觉得它们诱人且向往,且多半被体验为自然甚至不可避免”(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3)。这种意识形态的钳制力,尤其体现在对那些不健身的人的普遍态度上:他们被刻画为缺乏毅力与意志力。健身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可谓一种“健身号令”(fitness command;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5–6)。
此外,在现代隔间办公室的久坐生活引发的身体退化面前,女性之间共享着对“工作之身”的集体焦虑(Saval 2014)。在此语境中,对我的对话者而言,核心肌肉并非因其“稳定性”或“功能性强度”本身而被膜拜,而是作为一组可视化指标,指示一个人的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在像上海这样几乎人人要加班的城市,能自律到早上六点起床跑步、午休去健身房、晚上和周末把疲惫的身体拖去普拉提上课的人,会被钦佩,而这种钦佩的参照标准正是被核心肌肉越来越具身化的辛勤、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此外,一个辛勤且守纪律的身体应当被展示出来,比如把自己的锻炼过程与成果(练出核心)发到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
Cederström 与 Spicer(2015, 33–34)观察到,维持办公室人员“能量水平”的最大障碍,恰恰是身体本身,它构成“24/7 资本主义主体的核心挑战”。在关注企业打造更健康的工作场所与“适能”身体的项目时,他们指出(2015, 37):
一种解释是,让雇员参与健身课程有助于企业雕塑劳动力。在跑步机办公桌上不懈奔跑,更多是在生产一种理想工人。[…] 这就把“适能雇员”与“高产雇员”之间建立起一种强而有力的联系。(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在“适能/健康的雇员=高产的理想雇员”的形象支配下,“不健身、久坐”的人自动被视为不活跃且低产。“理想化的高产工人”已转化为“对锻炼上瘾的‘企业运动员’,他们白天能高效完成创意劳动,下班后仍能带领健身课”(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37)。
鉴于“成为高产雇员”与“保持适能身体”的深度关联,Cederström 与 Spicer(2015, 40)认为工作伦理已被“健身伦理”取代,尽管我在上海的民族志材料更显示某些白领女性身上“工作伦理”与“健身伦理”的并存。在此语境中,“锻炼(duanlian)”传达出辛勤伦理,并通过身体媒介指示自我发展。除了承担长工时与重负荷的工作投入(Peng 2020;Peng 2022),我的对话者还把时间投入到规律运动与体适能监测上,通过健身来“搁置这样的问题:她们是否是公司(或任何别的公司)会觉得够主动、够有活力的那种雇员”(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40)。在工作与身体上同时辛勤耕耘,“已成为当今世俗天堂——持续就业——的代价”(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40)。
有一次在普拉提课中途,老师冲着学员耳边喊:“把这个动作当成你的工作来做!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你会怎么做?你会放弃吗?!”课后我问几位女性如何看待老师把普拉提表现类比为工作表现的规训。有人半玩笑半认真地说,这让她们感觉如果此刻“动作失败”,就等同于“工作失败”。也有人评论说,工作伦理对她们生活各个方面的恼人渗透,包括锻炼在内。比如,一位名叫 Maggie 的年轻女性抱怨:她不仅晚上在家要回复老板的工作消息,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做一件看似与工作毫无关系的事——晚上去普拉提工作室锻炼——却仍被老师提醒,她“其实是在工作”。“你对24/7工作这件事无能为力: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健身房,做什么都是‘工作’。”Maggie 说。
这一幕呼应了 Cederström 与 Spicer(2015, 4, 36)的主张:适能的身体即高产的身体,模糊了“工作”与“锻炼”之界线。当工作成为锻炼、锻炼成为工作之时,我们会注意到曾被视为分离的“休闲与劳动”两类活动的融合(Cederström and Spicer 2015, 38)。锻炼(duanlian)意味着为了维持一种理想化的公司化、高产的身体而进行的劳动,并传达一种工作伦理与自我发展话语。在其对新自由主义时代“幸福产业”的批判中,Davies(2016)指出,多种“适能”“幸福”“生产力”“成功”的观念彼此混融,尤其当工作与健康的“物理性”与“心理性”相互交织时;在这些价值背后所支撑的人类理想存在形式,是“勤奋工作、幸福且适能”。当 Maggie 的普拉提教练在一个远离工作场所的锻炼时空仍告诫她们“你们当下是在工作”时,公司理性与工作伦理便渗入家与工作之间的时间与空间。在这里,通过有计划地把身体恢复到某一适能水平,来管理那个通过锻炼不断被发展出来的“高产之身”与“辛勤之我”。
女性“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与生育焦虑
我身边的白领女性认识到,面向企业化都市中国的职业女性中,“全都要”的话语越来越流行。作为有抱负、爱拼搏的职业女性,许多人感受到“全都要”的压力:一个成功女性应在工作中高水平表现,拥抱“女强人”形象;在家庭中做“贤妻良母”;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身材不能走样。西方女性名人畅销书的中译本,如 Sheryl Sandberg 的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与 Michelle Obama 的 Becoming,被许多都市职业女性阅读,从而强化了“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
曾任某德国汽车制造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的 Yolanda 认为,都市中国女性中“全都要”话语的兴起,也与一位中国女性名人李一诺有关。她在社交媒体上日益受到年轻人崇拜。李一诺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数学博士,后加入咨询巨头麦肯锡公司,仅用六年就一路晋升为全球合伙人,之后转至盖茨基金会担任高管。近年,她在北京郊区创办了一所“另类型”的学校,成为教育行业的社会企业家,同时也是凭借励志博客走红的社交媒体影响者。社交媒体上对她的常见描述包括:“有三个孩子、并且有马甲线的职业妈妈”;常见的视觉呈现是:她在车后座上用手机处理工作,同时用两只强壮的手臂抱着三个孩子。
尽管“全都要”话语盛行,上海许多女性仍在推迟结婚与生育,尽管国家已从“独生子女”转为“三孩”政策,并鼓励女性多生,以解决劳动力萎缩与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发现,已婚且生育的女性常在“工作—家庭—锻炼”的时间分配上苦苦平衡。回想开篇的 Chan——不仅迅速重返工作岗位,还在分娩与哺乳后“立刻找回核心”——我们就能体会到:对白领女性而言,训练核心的象征价值,与她们对生育将同时给事业与身体带来挑战的焦虑是并行的。在别处我也展示了女性生产与再生产角色之间的紧张加剧,以及她们对生育阶段身体变化的焦虑(Peng 2023)。
生育给白领女性带来挑战:事业晋升受阻的同时,身体也在“变大”。在上司眼里,女性的再生产角色意味着请产假、投入工作时间/精力/注意力减少,许多雇主借此为偏向男性的招聘与职场实践辩护。职业女性通过锻炼(duanlian)训练核心当然无法直接解决孕产哺乳带来的“生产力”挑战,但在生育阶段通过训练恢复体形,或能对付许多职场女性因身体表征的变化而产生的担忧甚至羞耻。核心肌肉象征着一些女性维系自己与“生产性工作领域”关联的决心,尤其是她们会特意训练那些最容易显露年龄与生育痕迹的部位。
当普通女性难以同时拥有事业、家庭与健美身体之时,“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中的榜样角色天然推广了女人在生活各领域的“理所当然的辛勤劳动”:办公室、家庭与健身房。对李一诺及其追随者而言,健美之身是一种受纪律约束的身体,它抑制欲望,具身一种辛勤、奉献与毅力的文化伦理(Carolan 2005, 97)。“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包括核心肌肉)把健美之身标注为女性的“生产性角色”而非“再生产性角色”的信号,把她安置在工作的公共领域,并证成她作为严肃、投入之劳动者的身份。女性一方面被期待完成妻/母的再生产责任,另一方面又力图保持体形与工作权,以维持其“严肃、投入的劳动者”身份。当被视为“生育阶段的生产力损失”有可能危及她们在职场的关联与位置时,职业女性的身体与锻炼(duanlian)成为生产与再生产问题交锋的场域。
然而,并非所有女性都投入这种“全都要”的追求——成功事业、幸福家庭与有核心的健美身体。我认识 Yolanda 时,她刚辞去德国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职位,开始自由职业。与之前的德国公司相比,她觉得自由职业的专业环境更“松”、竞争性更低。Yolanda 从未对强调核心价值的身体训练感兴趣,她拒绝顺从女性“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包括对“健美身体”的要求。像 Yolanda 这样的职业女性质疑,“全都要”是否可能?女性是否背负了过重负担,要去迎合这些被社会认可且具身化的女性成功与自我发展标准?
作为其对“全都要”话语拒斥的一部分,Yolanda 并不把核心肌肉视为自我规训与辛勤劳动的指示,也不把锻炼、以及在训练核心中“让身体吃苦”,视为自我发展的组成。Yolanda 或许是许多中国女性中的一个例外——她们往往要在工作与身体上同时努力,尤其当再生产角色可能妨碍她们对“身体之生产/规训”的贡献时。在此强调“生产主义”不仅越出职场而且投向身体的语境中,“生产性身体”被看作建立在辛勤与自我规训之上,而核心肌肉在职业女性共同体中则具身这一点,其训练过程也象征这一点。我在上海观察到的白领女性的身体与其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空间中的锻炼社会实践,成为公共/私人领域与其相应的生产/再生产角色张力被表达与演绎的场所。
结论
相较于以“节食与拒食”作为显性策略(Spielvogel 2003, 195),下班后通过锻炼追求核心肌肉,成为职业女性对传统女性气质诠释的矛盾性、以及其生命中生产与再生产要求之间张力的标志。当女性面对怀孕与分娩有可能对维持体形与保住工作的双重挑战时,“要有一副健美身体”的欲望被强化。对下班后的身体训练进行观察,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富有生产性、辛勤且受纪律约束的女性身体”,而不只聚焦其再生产阶段与经验的文化建构(Martin 1992)。
在国家于四十年前启动经济改革与对全球市场开放之后,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使“生产力”至上,把“不具生产性的身体”视为不合时宜、无法适配未来进步的残余(Hanser 2008)。因长期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损害而导致劳动力萎缩与人口老龄化,中国国家近年在悼念社会主义时代遗产的同时(Hershatter 2011),一方面敦促女性继续做“生产性工人”,另一方面也鼓励她们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做善于照看老人和幼儿的“好照护者”。社会再生产需求的提升,常令女性在职场处于不利,有的雇主以女性需要几年内多次产假、工作时间内哺乳、因家庭义务减少加班为由,正当化不雇用或裁撤女性。在遭受歧视性职场实践之外,一些女性也因不同生育阶段的身体变化而感到羞耻,并在努力守住工作权的同时,焦虑于如何保持身体的“适能/健美”。
基于我在上海一间普拉提工作室对年轻白领女性训练核心肌肉的参与观察,我发现:职业女性把自己的身体当作践行辛勤劳动、具身自我规训与自我发展的重要场域,并把锻炼(duanlian)作为一种正当方式,用以培养并将工作伦理延伸至工作场所之外。我将核心肌肉的社会性价值与当代都市中国职业女性中盛行的“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联系起来——这一话语塑造了她们在工作与身体上的双重用功。通过培育“完美的身体形状”(以核心的存在与形态为信号),这些女性在自我发展话语的驱动下,被看作严肃、投入且富有生产力的劳动者,也是受纪律约束、辛勤工作的人。尤其在生育与为人母带来职业与身体双重挑战之时,女性会格外努力,一方面守住工作权、另一方面维持体形,以回应社会同时提高“生产力”与“生育力”的要求(Peng 2022;Peng 2023)。更进一步,通过她们的锻炼——为把身体练“得体适能/够健康”而付出的辛勤劳动——女性构建出一个“自我与他者共同受规训”的社会空间,她们在其中把“全都要”的自我发展话语内化于身,将工作伦理延伸,并把企业精神的纪律性强化到越出物理工作场所的空间中。
当女性训练身体以贴近成功职业主体(健美且高产)的标准时,自我规训与辛勤的性情就被具身化,并从工作场所转置到家与工作之间的其他社会空间。在她们的日常锻炼社会实践中,白领女性的自我发展通过对“辛勤身体”的规训以及“群体性锻炼”的方式而实现。我希望未来研究能更加关注那种“通过工作来逃避工作”的尝试,它提示着当代都市中国与生产力相关联的自我发展之悖论。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