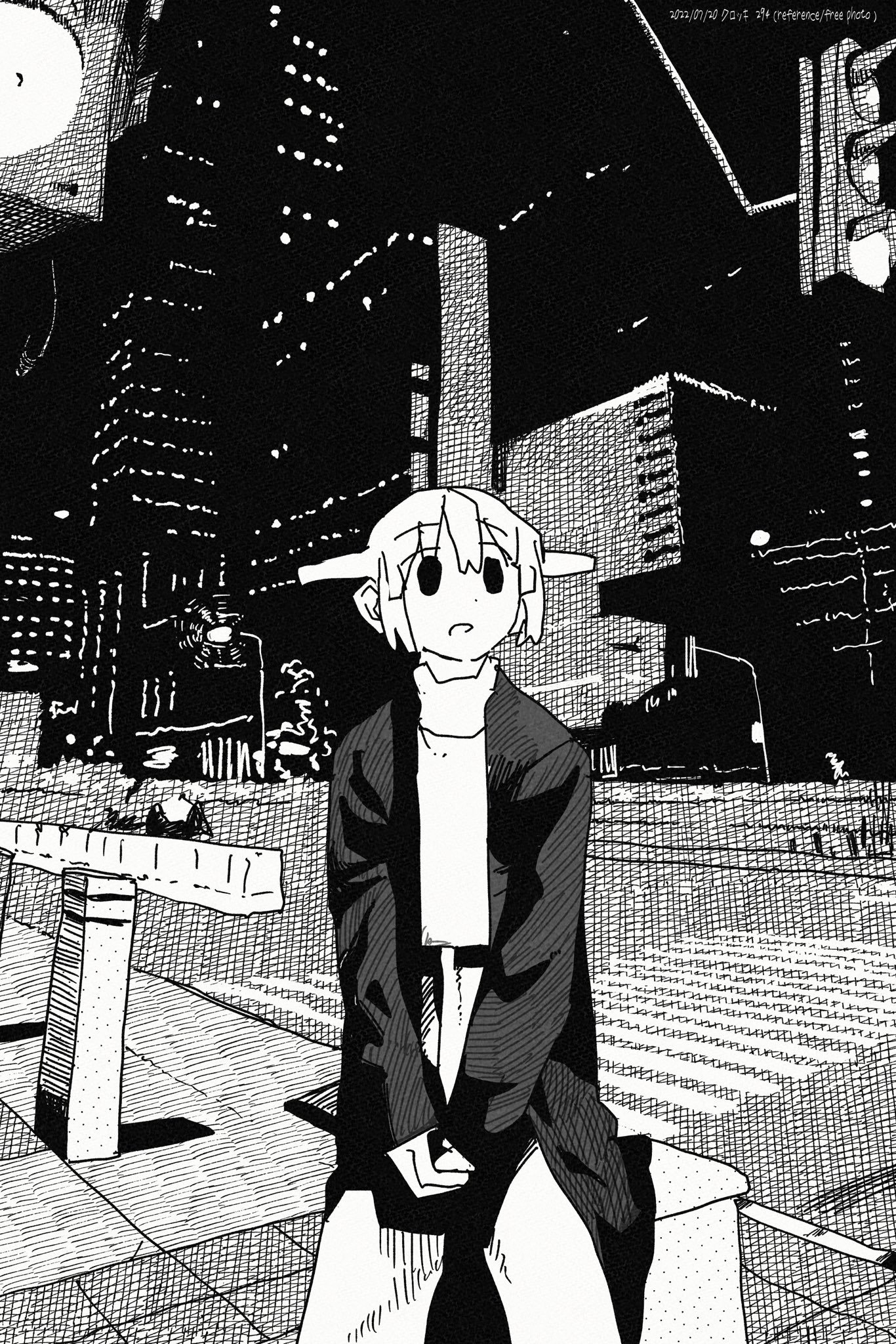在宿命与能动之间:“缘分”的概念及其在当代中国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中的作用
Self-Development Ethics and Pokitics in China Today第10章
在宿命与能动之间:“缘分”(yuanfen,“Fated Chance”)的概念及其在当代中国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中的作用
Isabel Heger-Laube
摘要:汉语中的“缘分”(yuanfen)最恰当的界定是“命定的机缘”,即通过某种宿命性的机会,使人与人,或人与物之间得以相遇与联结。缘分曾经是一种被动的归因,使个体可以回避承担责任;但在近几十年中,它愈发被赋予强调个人能动性的要素。就此而言,它契合“宿命能动观”(fatalistic voluntarism;Lee 1995)这一世界观:相信超出人力可控的力量与相信自我主宰并不互相矛盾,而是辩证地共同作用,帮助人们应对现代生活的变迁。本文通过对中国大学生的质性研究表明,凭借其辩证的特性,缘分可以成为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的一种独特资源。此概念所滋养的心态与儒家“修身”理想相通,不仅有助于个体在当代中国之现代性动态中积极前行,并由此在更广意义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关键词:宿命能动观,辩证思维,修身,文化心理学,治疗性治理 作者简介:Isabel Heger,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其现有研究(在天津东丽区开展田野)聚焦国家主导城市化在中国失地农民叙事中的角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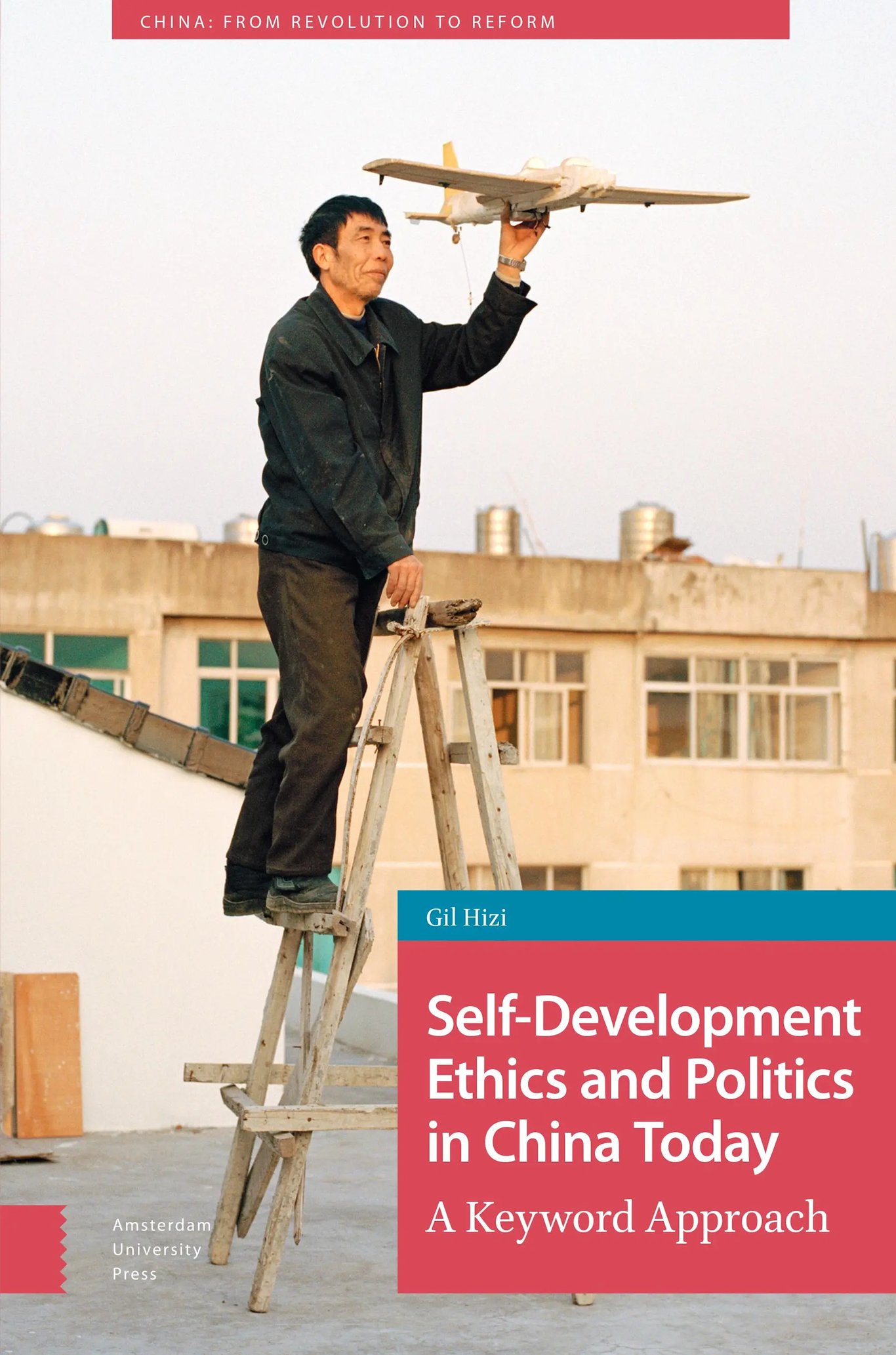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生活图景呈现为一种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不断增加的多元性、高度的地理流动性、上升的社会流动性以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并存。个体在很大程度上已从社会主义时期那种包揽性的社会结构、约束与保障中被“嵌出”,从而要对自己的命运负起全责,使自我提升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必须(Beck and Beck-Gernsheim 2010; Yan 2013; 2010; 2009)。塑造当代中国的这种现代性,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的路径、自由与机会前所未有,同时也意味着日益增长的成功压力,以及重重不确定、障碍与“玻璃天花板”。
正如一些学者(Fan et al. 2005; 2003; R. P. L. Lee 1995)在20世纪90年代就香港与深圳所观察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伴随的深刻社会经济变迁引发了有关意义的新问题,并要求个体发展出相应的应对机制。耐人寻味的是,为了应对现代性的处境,中国人开始重新阐释与再利用本国文化传统,作为实践与灵性指引的资源,将传统信念与概念调适为适合现代生活的工具。在国家推动的持续“心理热潮”(psychoboom)背景下——即一种由政府主导的“心理化”治理,将重心放在个体为自身心理健康负责之上,同时转移公众对塑造中国现代性的更宏观结构性问题的关注(Yang 2017; Zhang 2017)——将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心理资源的做法更为流行。此种“治疗性治理”的方式,促使传统哲学与概念被复兴为本土的自助与心理咨询资源(Wielander and Hird 2018; Yang 2017; Zhang 2015)。
中国人用以应对现代生活挑战的传统信念之一,便是“缘分”(缘分,yuanfen)。鉴于其历史积淀与复杂性,缘分在西方文化中并无真正对应物。较为贴切的界定,是指一种“命定的机缘”,借此人与人(或人与事物)被牵引到一起;或反之,视为一种条件性原因,缺失它某种关系或事件就可能不会发生。1 2 (译注:本文注释部分全部改成尾注形式,敬请谅解)由于能够对各类(人际)情境提供解释,缘分一直作为一种外部归因3 在华人语境中发挥积极功能。然而,缘分曾是一种允许个体回避承担责任的被动归因,而近几十年来,它日益包含强调个人能动性的要素。
在这种辩证性中,当代的缘分概念契合“宿命能动观”(suming nengdong guan),此理论由香港社会学家Rance P. L. Lee(1995;另见Lee P. L. 1995)提出。Lee认为,对超出人力控制之力量的信念并不与自我主宰的信念相抵牾;相反,二者在个体对现代生活无常的心理—社会调适过程中辩证互补。简言之,“宿命能动观”使人们一方面接受无法改变之事,另一方面坚持努力改变可改变之事。此外,Lee(1995, 52)强调,如今当人们将缘分4 等传统概念当作文化资源加以援引时,“其被动、宿命的涵义较少被强调,而其积极、行动性的涵义则更受重视。”这与相关研究相一致:在华人文化语境中——有别于源自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对命运等外在力量的信仰并不等于一种导致无力感、缺乏自我效能与消极性的宿命论世界观(Norenzayan and Lee 2010)。相反,对命运或“命运控制”5 的信念被证明能够促进能动性,增强个人驾驭感,并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S. X. Chen et al. 2006; E. Y. Liu and Mencken 2010)。
我对缘分能够在现代中国个体生活中发挥有意义资源之潜力的理解,起始于该术语在中国大学生日常语境中的“本土”(emic)使用。在我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ECNU)全中文班学习的一年(2010—2011)里,我屡次注意到中国朋友与熟人如何借“缘分”谈论其生活中的关系与事件,而这似乎对他们的心态有非常积极的影响。6 2012年,我据此观察回到华东师大,开展关于缘分对于内地大学生之意义与功能的质性研究(见Heger 2015; 2013),以此作为考察该概念在中国学生现实生活中角色的第一步。7
在本文中,我重访关于缘分的最初研究,旨在为当代中国青年成人如何在现代性的机遇与挑战面前安顿生活、理解自身(自我)发展轨迹之讨论,贡献相关见解。贯穿全文的理论线索,是“宿命能动观”的框架。首先,我将追溯缘分概念从传统根源到其当下形态的演变,并回顾其作为归因之功能的相关研究。随后,基于2012年在华东师大收集的数据,我将实证探讨缘分在中国学生生活语境中的作用,勾勒宿命与能动要素如何交织,帮助青年成人理解过去、应对当下并面向未来。在讨论部分,我将凸显:当缘分被作为文化资源加以援引时,它会培育与儒家“修身”理想本质相关的心态。8 我认为,这些心态不仅有助于个体的心理—社会调适,还可就塑造当代中国之现代性的某些挑战,促进社会稳定与和谐。
从“能动宿命观”到“宿命能动观”:缘分的演变及其在中国历史中的功能
“缘分”概念——最初仅为“缘”(yuan)——其源头在佛教,佛教首先于汉代(公元前207年—公元220年)传入中国。在佛教哲学中,“缘”指在“因”之外的助缘或条件,作为次要或情境性原因,对于产生某一特定结果至关重要。9 然而,自唐代(公元618—907年)起的“汉化”进程——即对佛教概念的世俗化、将其纳入既有世界观,以及普通人在日常意义建构中对其的运用——使“缘”成为中国文化的本土组成部分(Bai 2004; Jing 2005; Yang 1988)。10 作为汉化的结果,该概念也吸纳了道家与儒家思想的要素,并与所保留的佛教要素一同,至今仍各自影响着人们对其本性与运作方式的理解(Hsu and Hwang 2016; Liang et al. 2017)。
在历史演进中,“缘分”及其功能发生了重要转变,这可通过考察中国人世界观中宿命与能动之间关系的变化而得到最佳理解。正如Lee(1995)所解释,11 中国人的思维一直由宿命与能动的互动所塑造。12 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13 中,人们的精神生活浓厚,并倾向于“偏重”(pianzhong)宿命因素;而在现代中国社会,人们则日益重视个人能动的力量。Lee(1995, 248)认为: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描述为一种转变,即从传统的‘能动宿命观’(nengdong suming guan)向现代的‘宿命能动观’(nengdong suming guan 的次序倒置)。”
在传统中国,对“老天”预定个体命运的信念,以及众多迷信观念,牢固地存在并常被援引以解释超出个人控制的境遇。在此宿命式世界观之中,“缘”的概念在人的意识中扎根,被视为一种不可控的条件性力量,决定某一事件何时以及如何影响个人生活。14 类似于决定论式的“命”,个体必须被动、无力地接受“缘”的作用。然而不同于“命”,“缘”被认为仅在“人际关系”领域发挥影响,且可能带来好的或坏的结果15(Bai 2004; Jing 2005; Yang K. 1988)。可能是为强化其宿命色彩,唐代日常语言使用中在“缘”后加上源自“定分”(dingfen)的“分”(fen)这一音节,形成“缘分”(Bai 2004)。
据台湾文化心理学家杨国枢(1988;亦见1982;Yang and Ho 1988)指出,在传统中国“宗族中心的集体主义”社会现实中——在这种现实里,个体事实上并无多少个人生活抉择的自由——此一宿命信念对于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将关系的形成、发展、结果或其缺乏,归因于外在的“缘分”,而非个人特质、努力或责任,不仅帮助个体理解自身际遇并保护自我;更有助于避免与关系中他人(直接或间接)发生冲突并为他人“保全面子”。16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防止人们脱离其初级群体。杨(1988)推测,与这种“防御性理性化”相关的缘分之积极社会功能,在一个个体化社会中将会流失。
关于20世纪大部分时期此概念如何发展,以及它在民国时期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当传统信念与实践遭到清除打击之际——能够发挥何种功能,文献记载并不充分。然而可以推测,即便在意识形态高度限缩的年代,缘分信念仍持续存在于人们心中,并在意义建构中被援引为资源,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再度复兴(类似考察,见Fan et al. 2005; Liu and Mencken 2010)。
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与个体化的进程相一致——这些进程在1978年以后于中国大陆加速(Yan 2010)——“缘分”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多项研究(如Chang and Holt 1991; Heger 2015; Jing 2005; Liu 2010; Yang 1988; Zhang and Zhou 2004)显示,与早期不同,缘分几乎已失去迷信色彩,现今多被视为良性的。此外,缘分归因不再仅限于人际关系,而是扩展至人与地点、物件、动物以及工作、学业、兴趣等事物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缘分不再具有决定论含义。尽管仍被看作外在且不可控的力量,当代缘分概念为个人能动性留出了空间,并在某种意义上邀请与要求个人能动的介入。这一新观念清晰体现在“缘”与“分”二字在近时语义上的新解读:缘仍是被感知为带来某次相遇的外在力量,而“分”虽最初因强调决定论而被加于“缘”后,但现今常被解释为相遇的结果,或可由个人能动性所涉入的那一部分(见如Bai 2004; Hsu and Hwang 2016)。17
关于此一现代、辩证概念之心理功能,Lee(1995)在其“宿命能动观”理论论述中做了总体概括:缘分中的宿命要素帮助人们正向地理性化无法改变的过往结果;而其能动要素则帮助人们维持积极心态,鼓励在当下采取积极努力,并导向对未来的希望展望。为这一较一般性的理解,台湾文化心理学家许心萍与黄光国(2016)进一步补充了缘分如何促成心理—社会调适的理论洞见:作者通过一套试拟模型展示,当人们在处理人际问题时援引缘分,会引发动辩证思维之过程,徘徊于“认命”(renming),即在承受中转化思想的被动态度,和“知命”(zhiming),即主动调适以应对既定挑战之间。此过程的终点,是人们会采取达到心理—社会稳态的“最理想的应对行动”,这些行动皆属于“修身的期待”(Hsu and Hwang 2016, 2):忍耐(rennai)、宽恕(kuanshu)、努力(nuli)与(或)感恩(gan’en)。因此,缘分通过促发个体的修身过程,根本上促进心理—社会调适。
除上述理论性论述外,多项实证研究也揭示了缘分在其辩证性质下,能为华人个体发挥的多种功能。18 在人际关系领域,缘分不仅催化(亲密)关系的形成与推进,还帮助人们理性化负面的关系事件。此外,将之归因于缘分,使人们更加珍惜并主动经营生活中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缘分对社会互动发挥近乎规范性的积极影响,促进善意、尊重与和谐(如Chang and Holt 1991; L. Chen 2009; Heger 2015; Jing 2005; Lee et al. Lee 2012; Wang and Xie 2021; Yang and Ho 1988; Zhang and Zhou 2004)。就个人人生历程而言,缘分被证明有助于人们在不否认自身责任的前提下回溯性地积极理解挫折,引导其前行路径,激励其为目标主动奋进,帮助其适应变化,提供对未来的乐观展望,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促成个人成长(如Du 1999; Fan, Whitehead, and Whitehead 2003; Heger 2015; Li and Chen 2006; Li and Jin 2018)。
综上,既有的概念性与实证性研究为当代华人个体的缘分概念及其功能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仍明显缺乏一种研究路径,将有关缘分的发现与更广阔讨论相连接,即个体在何种结构性条件与话语环境中,将缘分当作心理—社会调适的资源加以援引。本文试图以当代中国的青年成人群体为例,向这一方向迈出第一步。
在宿命与能动之间:缘分在中国学生生活语境中对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的作用
中国的学生生活可被视为一个缩影,其中再现了塑造中国现代性的诸多条件与动态。一方面,它令青年成人面临与人际关系、个人表现与未来前景有关的诸多挑战。19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生生活也是青年成人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并很可能比今后任何时候——更多自由与闲暇的时期。于是,它成为在社会关系、爱情、兴趣与课外活动方面的探索阶段,同时也是对人生目标、梦想与价值进行反思的阶段。总之,无论是新的挑战,还是新的自由,都要求个体作出相应的调适。
如前所述,我在中国学生生活语境中所获得的民族志观察引发了我对“缘分”的学术兴趣,进而促使我开展一项关于该概念在中国大学生中的意义与功能的质性研究。本章所依据者,为我在2012年秋季于华东师大访学期间所收集的数据。总体而言,我对19位在读华东师大学生进行了半结构式质性访谈。20 需要强调的是,其中5位受访者的招募,意在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对照组”,21 即我希望了解:即便受访者事先并不知晓研究主题是否关于“缘分”,他们是否仍会提及“缘分”或类似概念;从而尽可能缓释这样一种可能的偏差(既有研究迄未关注):即参与一项专门关于缘分的研究可能对受访者的反思过程所造成的影响。所有访谈数据均以中文逐字转写,并在ATLAS.ti中采用菲利普·迈林(Philipp Mayring, 2010)的质性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
将缘分安置于青年成人的世界观之中
为评估缘分对于中国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该概念在个体总体世界观中所占据的位置。在以“基于个人境遇(例如家庭背景及其他结构性条件)努力奋斗、力求进取”为不言自明的准则影响下,我的受访者皆认为个人努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因素,相信人应当并且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目标、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gaibian ziji de mingyun)。在此背景之下,他们也承认有一些事情并非仅凭个人努力即可规划或控制——诸如超出个人行动范围的生活复杂性与偶然性,比如你将遇见什么人,或者你的努力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得到回报。这正是“缘分”发挥作用之处:据受访者的叙述,缘分在生活中的角色可被最恰当地理解为一种“辅助性配料”,当个人努力触及其边界时,它能提供解释与(或)鼓励——它能丰富生活,但绝不应该过度依赖,更不应以之替代努力。在一个恰切的比喻中,一位女性受访者将缘分在生活中的角色比作菜肴里的调味(调味剂;调料):
“嗯……它可以算是一种调味剂。比如你在做一道菜,如果没有盐或者类似这样的香料,这道菜就还称不上是一道菜。它是一种很重要的调味,但放多了也不好,必须恰到好处。”22
虽然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一般意义上相信缘分,但这种信念的强度以及他们赋予该概念的含义差异很大。有些学生叙述了许多他们归因于缘分的情境与关系,另一些则提到,除访谈情境之外,他们很少会想到这个概念。23 因而,就缘分对青年成人可能具有的功能而言,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功能并非源于一种笼统的文化性信仰,而在于个体是否赋予该概念以个人化的意义,并相应地将其作为心理—社会调适资源来加以援引。
无论学生在自身生活中赋予缘分多少意义,他们对缘分在一般人生活中的作用皆以“积极、主动”(jiji)来评估。尽管其源于外在,缘分并不被认为与个人能动性相冲突。24 虽然没有受访者认为缘分可以被直接操控或“创造”——它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你的生活总带有某种随机性——但关于缘分如何生成的看法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与他们对缘分的细微理解有关。25 有的学生认为,你可以——甚至必须——主动创造(创造,chuangzao)缘分进入你生活的机会。也有人认为,虽然不能主动创造缘分的机会,但你所做的一切会间接为它搭建一个平台。还有人则认为,你只能“遇见”缘分,行动无法对其产生影响。无论如何,一旦遭逢缘分,你可以——并且在多数情况下会——主动把握(抓住,zhuazhu)并珍惜(珍惜,zhenxi)它,以免错过(错过,cuoguo)。但你也可以决定不去追求,或者让其“顺其自然”(shunqi ziran)。26
我的受访者将各类关系、事件,或与地点、事物的联结归因于缘分,这些经验具有三个共通特征:第一,它们是积极的,或被有意地视为积极的,或虽未如愿展开却在事后被积极地看待。纯粹消极的事件,如有归因,也仅归为“缺少缘分”。第二,所有被归因的经验对个体具有主观意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它们都带有某种不可控与偶然性、某种不可解释或无法完全以理性解释之处——一种“偶然”(偶然,ouran)的因素。相反,能够完全以个人努力或个人失败来解释的事,从不被归诸缘分。
总体而言,不少受访者意识到缘分对其知觉与行动所产生的积极或转化性影响。这些学生在无意间描绘了这样一个过程:该概念以其辩证性,启动了令其“修身”的历程,并促使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例如,一位女学生反思道,生活中会发生一些并非自己计划之内的事,而个体的职责是把它们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并据此应对:
“通常,人生里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为此必须做什么。但缘分是由某种偶然所决定的——你不知道它何时发生,也不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是好是坏。就像我刚才说的,当缘分进入你的生活,你会去接受它。然后你就会知道该做什么……如果是好事,你会抓住并珍惜它;如果不是好事,你会学着改变它,或者改变自己,或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变对方。”27
最后,同样颇为有趣的是,有些学生谈到,他们有时会“有意识地”将生活中的关系与事件归因于缘分,以便在自己心中培育积极情绪与积极心态。也就是说,即便在尚未经历某种可使之“事后识得缘分之作用”的积极转机之前,或在缺少常被描述为伴随缘分相遇而来的那种深切“亲合感”的情况下,28 他们也会有意识地选择相信某事由缘分所致。回到“缘分是生活中的辅助配料”的比喻,一位女受访者把缘分比作一种可以在感到无力时用来调适自我的“调味料”:
“在人际关系方面,如果我把它们当作缘分,这会让我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也像是一种支撑的力量,让我想去珍惜和保护这种感觉。……至于生活中碰到的其他事情,像工作或学习,我可能更常是有意地用‘缘分’去尝试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某些负面的处境。之后我会想,其实我所遇到的这种情况,有点像是冥冥之中(ming ming zhi zhong)的巧合,这会调节我的情绪,给我一些鼓励。……它就像一种调味料,它不是[生活中的]主料——但在合适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调一调自己。”29
理解过去
作为一种回溯性归因,缘分帮助我的受访者:要么理解他们过去那些格外积极的事件,要么理解那些没有按他们原本意愿或期望发展的经历——但这些经历最终被他们以积极的方式学会接受。前一种情况下,将之归因于缘分会进一步凸显一次相遇或事件的正面意义;后一种情况下,则强调可以从挫折中汲取的积极之处,而不是同样可能被汲取的消极之处。就缘分对于青年成人心理—社会调适的作用而言,只有后一类经历值得我们关注。30
过去经历中,一类能通过“归因于缘分”而凸显积极性的,是失败的恋爱关系。正如一些学生解释的,他们与前任未能继续在一起这一事实,并不抹去一种认识:曾经有一种特殊的机缘把他们牵到一起。通过仍把这段关系的形成归结为缘分,他们得以温情地回忆彼此共度的美好时光,尽管这种幸福并未注定长久。然而,被归因于缘分的过去经历中最常见的,是学生们走向某个专业或某所大学的曲折历程——这些在当时被视为重大挫败,但出人意料地,许多学生事后将其看作积极的转折点。这包括不得不复读高考、心仪大学未录取、或被分配到志愿表里根本未填报的专业。31 例如,一位女受访者原想在本科攻读日语或英语,却被分配到学前教育专业——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她班上的学生无一是主动选择该专业的。她叙述说,自己最终学会了热爱这个专业,甚至在研究生阶段决定继续深造:
“其实我经常回想[我的学业路径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可以说有点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32 ……所以我觉得,起初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后来我慢慢开始喜欢,而到现在我不仅接受了它,还非常热爱这个专业——我觉得这像是上天的安排。33”
显而易见,将之归因于缘分并非对命运的被动接受,而是一个主动意义建构过程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把某些(失败的)关系或人生挫折理解为“本就应当如此”,帮助学生对自己人生所走出的特定轨迹作出积极理解,而不是心存负面情绪或执念于“本可以如何”。此外,虽然把未如所愿的结果解释为外在的缘分是一种积极的、被动的合理化,能够保护个体自我,但这并不排斥个人能动性对这些结果的贡献。事实上,我的部分受访者甚至把他们归因于缘分的结果视为某种(业报式的)对个人努力的回报——尽管尽力而为未能得到最初期望的结果,但某种更高的力量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也许更有意义的机会。重要的是,许多学生在思考未来时也延续了这种心态。
应对当下
在应对中国学生生活的当下时,缘分展现出多方面的积极功能。其一,对缘分的感受(或有意识地将之归因于缘分)促进新关系的形成,并培育对既有关系的珍惜与积极态度。其二,对“可能邂逅缘分”的思考,能使个体对新的人际与经验更为开放,并鼓励他们为自己主动创造机会。其三,将某些无法仅凭个人努力改变的不如意状态归因为“缘分未至”,有助于青年成人在保持积极心态的前提下,妥善应对其个体处境。
若受访者认为某次相遇出于缘分,他们便会尽最大努力去珍惜这段关系。通常,被归因为缘分的(亲密)关系,不仅带有偶然与机缘之感,也伴随强烈的“投缘”。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我的一些受访者还在更基础的意义上将与特定他人——甚至与“人”总体——的相遇视为缘分,理由是“相遇本身即是一种珍贵的机缘”。这种心态几乎为他们提供了一套与人相处的伦理准则。这在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他们所归为缘分的宿舍舍友相遇34——这类关系并非出于选择,却在其生活中举足轻重。即便缺少特别的“投缘”,35 将其归诸缘分会让他们更看见对方的可取之处而非缺点,从而帮助学生培养更包容、更欣赏的态度。比如,一位女受访者告诉我,她其实并不太信缘分,但仍认为在生活的某些领域应该相信它,其中之一便是为了主动促成与舍友之间的和谐:
“生活中,我觉得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有时候,事情真的就像是上天的安排——不对,也不能说是上天的安排,就是一些偶然发生(ouran fasheng)的事。比如,我不能选择我的舍友是谁,但我可以主动去和他们建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怎样与他们相处]主要取决于我自己,但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缘分。36”
除鼓励学生主动经营既有关系之外,“也许会偶然邂逅缘分”的观念,以及在某些人看来“有责任主动为缘分创造机会”的信念,也对他们的心态产生了重要作用。无论哪种情形,与其被动等待缘分到来,“缘分”的念头都会提升他们去结交新朋友或寻找恋爱对象的动机,推动他们更外向、更勇于尝试新体验。最能体现这种主动姿态的例子,来自一位男受访者转述他在一次团体训练课程里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一条建议:
“每门选修课都找机会坐在一个不认识的女生旁边。这样你可以多了解她一点,也能多交几个朋友,而且不知不觉(bu zhi bu jue)中,这还可能带来各种不同的结果。37”
最后,将那些无法仅凭个人努力就改变的不如意处境(主要在恋爱方面)归因为“缘分未至”,对我的受访者也具有积极功能。这种归因使学生能够在保护自我、获得心安的同时,接受或忍受当前处境,并继续坚持为自己改变境况的努力。沿着这一思路,一位男受访者解释他如何看待自己尚未找到女朋友这一事实:38
“还有一些人,如果还没有遇到爱情,就会说‘缘分还没到’,这会让他们再多坚持一下。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只是觉得缘分大概还没来。如果你总是焦虑地看着已经谈恋爱的同学,你就会着急自己也要谈一段。但是因为[你承认]自己的处境和他们不同,你反而会更坚持自己的节奏与态度。39”
面向未来
最后,作为一种前瞻性归因,缘分对青年成人也展现出重要的积极功能。当然,“缘分”的念头并不能抵消受访者对个人与职业未来的所有焦虑;然而,它能促使他们以更为乐观的态度面对未来。此概念的前瞻功能,皆与这样一种信念相关:尽管你无法规划或控制缘分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你的生活,但当它到来时,它将是积极的,或至少会带来有利于个人成长的积极挑战。一方面,这一观念使受访者更容易接受——甚至欣然欢迎——人生中有些事纯属偶然;另一方面,若他们相信缘分是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生成”的,这一信念会带来自信与从容:即便无法掌控最终结果,他们的努力也会以某种方式结出果实。
首先,无论受访者是否认为个人努力可以间接“创造”缘分,“它也许在任何时刻意外进入生活、并带来积极影响”的念头,都为那些无法预先规划的未来结果赋予了乐观色彩。耐人寻味的是,这种心态不仅让青年人更积极地面对“未来可能很具挑战”的前景,也让他们更积极地面对“未来事实上可能非常单调”的前景。下面这位男受访者便说明,他相信缘分能够让枯燥而疲惫的职场生活——那种会一点点消磨人的斗志并使人身心俱疲40——变得更明亮、更有色彩。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受访者在读研前曾工作了一年:
“我觉得[由缘分所带来的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可预测的事,那就太无聊了(笑)。比如……如果你一个月要上29天班、只休一天,你肯定会想,‘哇,好辛苦啊!’……晚上下班在路上的时候,你会想,‘明天还要上班。’但如果你意外地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或者意外地遇到一个跟你特别合得来的人,……我是说,如果你相信缘分的存在,它常常会在很意外的时候出现……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当下的处境。其实这种东西——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未来——对我们的生活总是很好的。因为一种一成不变(yi cheng bu bian)、卡在老套路里的生活,比什么都无聊。41”
其次,在那些认为个体可以间接“创造”缘分的受访者那里,对这一概念的信念使他们在“寻找人生路径”上更自信、更从容。学生们承认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由个人完全掌控,同时相信借助缘分,他们的努力终将以某种方式得到回报,即便不是最初所设想的那一种。这种思路——一方面鼓励个人努力、让学生对出其不意的结果保持开放,另一方面预先保护其自我不被可能的挫折所伤——可以视为青年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特别是就业情境)的前瞻性应对机制。这在一位女受访者的叙述中体现得尤为清楚:她从江西农村的寒门背景一路走到上海读硕士,其轨迹充满了结构性约束、挑战与转折。似乎,她的过往经历对她的人生观留下了深远影响:
“我非常相信通过个人努力去改变那些可改变之事的力量。但同时也有一些……就是一些你无法改变的外在因素……我个人很相信缘分——比如,为什么我没有被第一志愿录取去学医,而是被第三志愿录取去学英语,后来又来到华东师大读教育类的研究生?至于未来,也许我会成为一名学者,也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普通的英语老师——我觉得不管[上天]有什么安排,我都会很从容地接受,因为我认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那一份努力。42”
讨论
在当代中国青年成人的世界观中,“缘分”的概念最可用“生活中的辅助性配料”这一隐喻来描述:它既不能也不应替代个人努力这一根本性角色,但就其作为由某种更高力量所决定的“命定的机缘”而言,它能针对那些无法仅凭个人能动性来解释或控制的人际关系与事件,提供解释、意义与指引。然而,缘分对中国青年的作用并不可一概而论。正如本研究所示,尽管青年人普遍在一种一般性的、文化性的信念层面上将缘分纳入其世界观,但只有当个体赋予它以意义,并在自身生活语境中将其作为一种归因来援引时,该概念才可能发挥积极的心理功能。有人很少甚至从不把缘分用于归因;也有人在意义建构的过程中频繁动用它。对于后者而言,缘分可成为一种独特的心理—社会调适资源,其社会意涵远超个体心理层面。以下讨论将进一步展开。
作为一种归因,缘分被证明有助于中国青年人积极理解过去的挫折与转折点;以更珍惜、开放、主动的方式应对当下;并以更乐观、从容、乃至更自信的姿态面向未来。与Lee(1995)的“宿命能动观”理论相应,使缘分成为应对现代生活诸般变迁的有力资源者,正在于其宿命与能动两要素的辩证互动。无论青年人是在(亲密)关系问题上,还是在自身发展轨迹上援引缘分——在每一种情形中,其“宿命”要素使他们能够对不可改变之事予以积极的接受,甚至欢迎不可控之事;而其“能动”要素则强化自我效能感,鼓励其持续努力。从更深层看,正如许心萍与黄光国(2016)所提示,缘分归因中宿命与能动的辩证互动,通过培育与儒家“修身”理想本质相连的心态与行动——如忍耐、安于命分、感恩、仁爱、宽容,以及自我精进与开拓视野的努力——帮助青年人重建心理—社会稳态(另见Matthyssen 2018; Wu 2017)。43
由缘分所滋养的这些心态,往往辩证地协同运作,对于帮助青年人积极驾驭中国现代性的诸种动态尤具价值——这种现代性一方面要求个体对自身命运负全责,并在理论上提供无数实现“美好生活”理想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个体面临诸多超越自身控制的挑战与结构性掣肘。在此背景下,缘分能够帮助青年人积极应对其发展轨迹中的挫折,或有关个人与职业未来的不确定性。除了承担重要人生事件的应对功能之外,该概念在日常层面亦具意义:它促使青年人培养一种对生活及社会互动之偶然性与变数更为积极、宽和的态度。
耐人寻味的是,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缘分不仅通过其对个体知觉与行动的积极作用而受益于个人,也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而,与杨国枢(1988)的早期判断相反,这一概念似乎并未在个体化社会中丧失其社会功能。相反,它如今之所以似乎能够促进社会和谐,正是通过其宿命与能动的辩证互动,而非作为一种被动的社会凝聚理性化。这一点在当代中国青年生活的两个重要领域中尤为典型:其一,缘分既激励人们为目标努力奋斗,又滋养对那些并未如计划展开的人生路径的安适与满足,由此支持青年应对与中国竞争性的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关的各种挑战与挫折,且重要的是,并不使他们从根本上质疑这一体制本身。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缘分如何帮助许多学生积极理解高考之后“非本意”的录取结果。将之归因于缘分,使他们能够以更正面的眼光看待当前处境,而不是执着于其他可能结果或怀抱怨怼——后者可能会引导他们去质疑中国不透明的高校招生体系,或更一般而言质疑当下中国的机会不平等(另见Heger 2017)。其二,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另见Wang and Xie 2021),把关系归因为缘分几乎为青年人提供了一套与人相处的伦理,从而可能预防因人际差异而生的冲突。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是一些学生如何援引缘分来培养对宿舍舍友——由系统分配而非自主选择的同住者——更为宽容与欣赏的态度:他们无法选择与谁同住,但既然选择相信缘分使他们相聚,便有意识地努力与对方建立和谐关系。
最后,还有一项观察值得进一步讨论:许多中国青年不仅意识到缘分对其心态的积极影响——换言之,意识到这一概念的“治疗性”品质;44 更有甚者,一些人还在特定情境中有意援引缘分,以在自身之中培育积极心态——即便并不真正相信某一结果“本就该如此”,或并未感到常与缘分相遇相伴的那种强烈亲和之感。将缘分作为修身资源的这种有意使用,不仅仅是青年人在应对与意义建构实践上的新趋势。我主张,这些实践是受前述由政府主导的关于幸福、积极心理学与自助的论述扩散所形塑,而这些论述伴随中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见Wielander and Hird 2018; Yang 2017; Zhang 2017)。我在华东师大就读与随后开展研究期间,对许多学生普遍关注“培养积极情绪、积极思维,并让生活充盈‘正能量’”(见Hird 2018; Hizi 2021)印象深刻——也即,关注个体如何或应当主动照料与培育自身福祉的路径。看起来,这些旨在塑造韧性强、自我负责、能够在快速变化且充满承诺、不平等与不确定性的竞争性社会经济环境中“自我治理”的主体之官方话语,已在中国青年人的现实生活与心智中找到沃土。显然,这也影响了他们将缘分作为归因的使用方式。
总之,本文表明,“缘分”这一概念能够在当代中国青年成人的心理—社会调适中发挥重要作用。凭借其独特的“宿命—能动”辩证互动,缘分得以培育与儒家“修身”理想本质相关的心态,这些心态不仅帮助个体积极驾驭中国现代性的动态,而且还可进而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此外,从中国青年在是否以及如何将缘分融入其生活方面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判断,该概念似乎正从一种几近普遍意义的文化信念,进一步演变为一种对每个个体均有不同意义、且日益被有意援引为心理—社会调适资源的文化信念。这一发展不仅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持续的现代化与个体化进程本身相关,也可能与塑造这一进程的政府主导话语环境相关——该环境将结构性问题“心理化”,并将心理韧性与福祉转化为个体自身的责任。

注释
——————————————-
1 我将 yuanfen 近似翻译为“命定的机缘”,并非随意为之。事实上,此译法最能概括当代概念所具备的宿命与能动两种要素的共存。形容词“命定的”传达出当人们谈到缘分时,有一种外在、不可控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名词“机缘”——其意涵兼及巧合、运气、概率、机会或“机遇巧合”(serendipity)(但无一词可完全穷尽其本质)——则表明,由缘分所促成的相遇或事件被视为一种可被个体把握或珍惜、也可能被错过的机会。
2 缘分作为“条件性原因”的本质,可由这句谚语最为贴切地捕捉:“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you yuan qian li lai xianghui, wu yuan duimian bu xiangfeng)。
3 “归因”是指为事件或行为寻找理由与因果解释的心理过程。人们对其生命经验所归之因,可在“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指外部或在个体行动范围之内)、稳定性、可控性”等维度上加以区分,并会影响其如何感知与应对这些经验(Bierhoff 2002; Weiner 1986)。
4 Lee(1995)举出的“宿命能动观”例子还包括中国的“忍”(ren,容忍/忍耐)这一概念、风水考量,以及对谐音(xieyin)的运用。
5 事实上,“宿命论”(认为事件预先被决定、个体无力改变)与“相信命运”(认为个体命运在某种程度上由更高力量所决定)并非同一事物。沿此理解,“命运控制”(fate control)可被界定为:“一种对生命事件预定性的信念,同时相信通过诸多实践仍有可能对这些结果施加影响”(Chen et al. 2006, 27)。
6 我第一次接触“缘分”是在一次校园散步中,两位女同学在谈论她们之间那种不可思议的机缘,使她们相识并成为挚友:她们来自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却不仅进入了同一所大学、同一专业、甚至同一寝室,更巧的是她们姓氏与名字完全相同——对她们而言,除了用“缘分”之外,别无他法解释此一切。另一次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偶尔参加的英语角上,当晚话题是“各自走向华东师大的路径”。一位男生讲述的故事显然引起了许多人共鸣:他未能被第一志愿的高校录取,而是来到华东师大——他的一所备选。起初,他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沮丧;然而,在华东师大获得诸多积极经验之后,他事后将这一转折视为“缘分”。
7 我于2012年为完成硕士学位而开展的研究(见 Heger 2013)触及了一个至今仍在的研究空白:虽说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或香港的学生因易于接触而多被纳入缘分相关实证研究的受访群体,但这些研究在解释结果时几乎都未真正将受访者的现实生活处境纳入考量(仅举数例,见 Chang and Holt 1991; Chen 2009; Hsu and Hwang 2016; Li and Jin 2018; Liu 2010; Shu 2018; Yang 1988)。
8 儒家“修身”(xiushen)的理想可理解为个体一生所进行的寻求心理—社会均衡之过程,即与自我、社会与天地万物相安。追求修身,核心即在于培养那些有助于提升人格德性、维系和谐社会关系、并在生命偶然性中寻得意义的诸德(Hsu and Hwang 2016; Matthyssen 2018;亦参见本卷 Hizi 的导论)。
9 有关其背后的佛教教义之详细分析,参见 Bai(2004)。
10 有关“缘分”概念的历史与语义演变之综述,参见 Heger(2015; 2013)。
11 这些解释仅见于Lee关于该主题的中文版本(Lee P. L. 1995),英文版本(R. P. L. Lee 1995)并未收录。
12 人们一直既要依靠自身以求生存与发展,同时也一直承认更高力量的存在。
13 Lee(1995)与其他华人作者所称的“传统中国”或“传统中国社会”,在一个宏观社会学意义上,可最好地把握为“前现代”中国;相对之下,“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分化、思维的理性化、传记的个体化,以及自然的驯化(参见 Brock 2011; van der Loo and van Reijen 1997)。
14 关于自唐代起“缘”的传统观念及其起源之信念,杨国枢(1988;另见1982;Yang and Ho 1988)曾通过对“稗官野史”、传说与早期通俗小说的分析予以重构。
15 后者即所谓“孽缘”(nieyuan)。
16 例如,将不幸的婚姻归因为外在的“缘分”,不仅可使夫妻二人,也是其家族以及参与撮合婚姻之人,免于因追究关系发展之真实原因而带来的罪疚或羞耻;反过来,将幸福的婚姻归因为“缘分”而非个人德行或努力,既可让这对幸福夫妻免遭他人嫉妒,同时也给那些未获此等婚姻福祉者保留面子。
17 当代概念的这种辩证性,清晰呈现在诸如“缘本天成,分在人为”(yuan ben tian cheng, fen zai ren wei)或“有缘无分”(you yuan wu fen)之类的表达中(后者常用以合理化为何一场相遇未成关系,或一段关系未能长久)。
18 其中一些研究涉及“宿命能动观”的框架,另一些则未涉及;无论如何,结果均显示当代缘分归因中宿命与能动两要素的共存。
19 首先,学生需要适应高校校园这一陌生的社会环境,以及宿舍生活这一有时颇具挑战的居住情境——来自不同地域与习惯的人汇聚一室。其次,一些学生仍需面对中国竞争激烈的全国高考之后并不理想的录取结果;此考试虽在理论上强调“唯才是举”,但实际又受地区与省份差异以及不透明的录取机制所形塑,进而影响个体成功的几率。其三,关于从高校到职场的过渡会引发疑问与不确定:随着高等教育扩招与合格劳动力的过剩,尤其出身较不优越的学生,往往难以找到匹配的岗位(参见 Bao and Li 2014; M. Fan 2011; Heger 2017; Howlett 2021; Liu 2009; Xiong, Yang, and Shen 2022; Yao et al. 2010; Zhang and Yu 2010)。
20 受访者年龄介于19—24岁之间。19名学生中,女10人、男9人;本科生11人、研究生8人。研究地点的有利条件使样本得以高度多样化:其一,作为国家重点高校,华东师大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不同于本地生源占比较高的省属院校;其二,华东师大为综合性研究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其三,“师范大学”注重师资培养,面向未来教育者的相关学科学费较低或予以减免,能容纳较弱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其四,我样本中的研究生均在他校完成本科,因此也将其他(多为名气较小)院校的录取与就读经历纳入了分析。受访者表格概览参见 Heger(2015; 2013)。
21 对该“对照组”,研究的真实主题仅在一组叙事提示之后才被揭示;这些提示也是对常规样本访谈的开场部分。我起初告诉相应学生,我正在做一项关于他们进入大学之前的人生轨迹及其学生生活经验的叙事研究,请他们讲述其路径与经验,并回顾人生所走之路与其总体世界观。在对照组学生获悉研究主题之后,访谈的余下部分照常进行。
22 访谈7:女,22岁,山东省,城市户口,音乐教育本科四年级学生。
23 这些个体意义的差异在对照组访谈中特别明显:如果“缘分”及相关信念(如“上天”或因果报应)对个体确有某种意义,即便事先不知研究主题,他们也会在叙述中提及——这类情况在5次中出现了3次;另两次则未提及“缘分”或类似信念,且在告知研究主题后,学生仍未回忆起任何他们已经或将会归因于此类信念的经验。总体而言,约半数受访者在其生活中赋予“缘分”很大的意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该概念在生活中具有积极但并非重要的作用;另有约四分之一则完全不赋予“缘分”任何意义。在我的样本中,就“强烈信念”的表达而言,女性占多数;而在不赋予该概念显著意义者中,以持高度理性生活观的男性为多。
24 仅有一位受访者与这一普遍共识显著相左——据他所言,尽管缘分及类似信念可能是积极的,但会导致消极被动,因此他有意并彻底地将其排除在生活之外。他用成语“守株待兔”表达其看法,喻指“坐等好运降临而不主动努力”。
25 虽然受访者谈论“缘分”时心中所指大体一致,但他们对其本性的构想颇为不同:有时更接近其佛教渊源,有时则更明显地受到道家或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细微的观念差异在不经意间显露出来:既出现在学生对“缘分”意义的描述中(他们常借成语与谚语表达),也出现在他们叙述自我所归为“缘分”的亲身经历时。限于篇幅,本文不展开讨论这些差异;详析参见 Heger(2015; 2013)。
26 重要的是,即便是看似被动的“放下”“退一步”或“积极地接受命分”,在更深层次上也包含能动、选择与意义建构的成分。关于其他具有相似辩证特质的“中国生活智慧”的相近见解,参见 Matthyssen(2018)。
27 访谈12:女,22岁,河南省,农村户口,中国教育史专业硕士二年级学生。
28 这种深刻的“投缘之感”常见于恋人、至交,或同乡(laoxiang)之间的偶遇等情境。
29 访谈13:女,22岁,河南省,城市户口,心理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30 就那些被归因于缘分的“格外积极”的过往经验或转折点,受访者叙述了各种“机遇巧合”的邂逅或令人回报丰厚的事件。例如,一位曾在读研前工作一年的男生,讲到他与最终录用他的公司人事主管的一次偶遇:某次返乡的火车上,他与身旁的男子愉快交谈,未留任何联系方式便分别。后来在该公司最后一轮面试时,他突然认出了这位男子——而对方也记起了他。自此之后,一切进展顺利。
31 此常见现象的中文术语为“被调剂”(bei tiaoji),字面意为“被调整”(有关更多说明见 Heger 2017)。
32 此谚语用以说明祸福之间不可预见的因果关联,流传版本不一。我的受访者如此解释:“古代有位老者养了很多马,一天,马都跑了——这本是大祸;但不久后,农场起火——若马仍在,必遭焚死。又有一日,这些马自己都回来了,安然无恙。于是老者意识到,马之出走,实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另见 Matthyssen(2018)对该俗语辩证内涵的探讨,强调将“循环往复”视为人生常态的中国心态,这有助于达致内心的平和。
33 访谈2:女,24岁,湖南省,城市户口,学前教育专业硕士三年级学生。
34 在中国高校宿舍里,尤其在本科阶段,最多可有多达8人合住一间小寝室,这并不罕见。
35 当然,也有一些舍友的“配对”被归因为缘分,理由是真正的“投缘”,或是因为星座相合——在部分女生看来,这些都是“二人有缘”的指标。
36 访谈15:女,20岁,安徽省,城市户口,对外汉语本科三年级学生。
37 访谈10:男,21岁,海南省,城市户口,心理学本科三年级学生。
38 有趣的是,受访者并未提到他们会在恋爱问题上以“缘分未到”的归因来保护他人的感受。仅有一位受访者(即下例引语中的同一位)提到,女性在结束关系或拒绝追求者时倾向于以“缘分”为借口。
39 访谈4:男,22岁,甘肃省,农村户口,物理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40 该受访者的描述,与“内卷”(neijuan, involution)的观念高度契合(参见本卷 Qian 与 Bram 的章节),但在2012年访谈时,“内卷”一词尚未进入青年人的日常语汇。
41 访谈5:男,24岁,河南省,农村户口,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硕士二年级学生。
42 访谈1:女,24岁,江西省,农村户口,高等教育专业硕士三年级学生。
43 这些洞见一方面印证了许心萍与黄光国(2016)所提出的辩证模型的初步设想,另一方面也将其适用性扩展至人际关系之外的领域。
44 关于“缘分”的“治疗性”品质,不仅可由中文互联网中数不清的相关博文以及通俗哲思著作中的大量讨论所证实(如纪 2010;王斌 2004),且基于显示缘分可用作自助资源的实证洞见,已有若干作者(如 Heger 2013; Hsu and Hwang 2013; Y.-C. Lee, Lee, and Lee 2012; D. Li and Jin 2018)探讨其作为本土咨询资源的潜力。然而,就“缘分”在心理治疗实践中的实际使用,目前似乎尚无证据可循。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