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症與個體的共生關係:Andrew Solomon 《正午惡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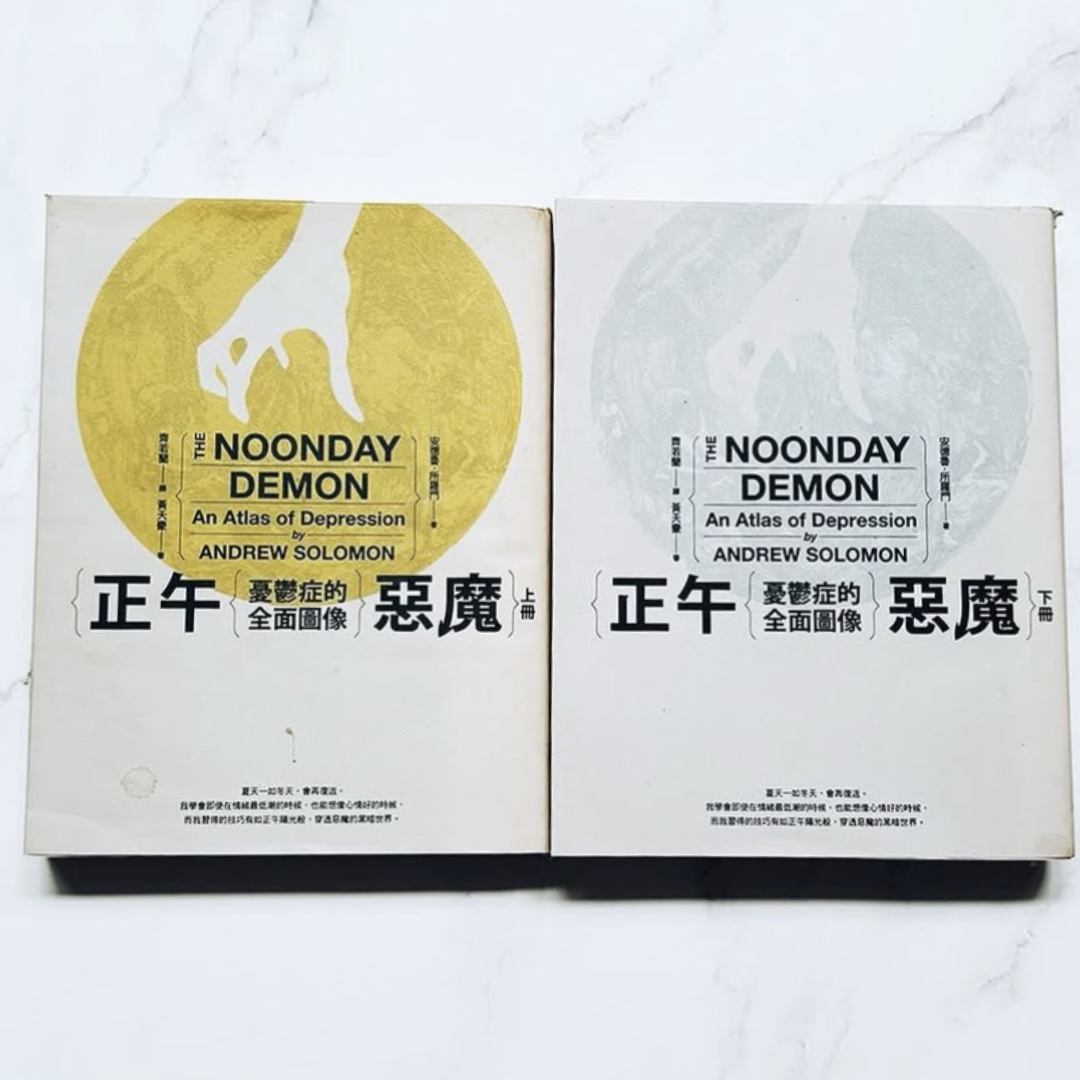
「寫書探討憂鬱症時,要避免將憂鬱症美化或妖魔化都很不容易,從某個角度而言,兩種錯誤我都犯了。但也許這樣的寫法才是最誠實的寫法。」
所有被貼上的標籤,都是個人與社會不斷鏡射而成的最終結果。
憂鬱症是我再熟悉不過的標籤,它是我的一面面向、一面真實,一個拿來觀看外界的稜鏡。
Solomon 描述憂鬱症的糾纏有如緊緊繞著樹幹、吸取養分的藤蔓;憂鬱症纏繞自我意識與認知,侵犯每一個生活空間,把個體榨乾取盡。然而許多情況下,藤蔓與樹幹是共生關係,如同憂鬱症與個體。共生,因為每一次的重新振作,意味著多一次機會在傷痕累累的蓊鬱中找出共存的策略。
憂鬱症就像是在時間軸的切片與切片中等待下一次的再見。我傾向認為,等待是為了讓自己做好準備。我兀自猜想,憂鬱症的人或許比較能理解人們口中的樂觀或悲觀,不過是些沒有被清楚定義的感受性贅字而已。真實、或前述所言的稜鏡映射,都期待可以被串連、被歸因、被收納,且並不帶樂觀或悲觀色彩;解構與分析,是我在憂鬱症學會最重要的謀生技能。
Solomon 提到,透過知識的獲取,讓他通往接受憂鬱症的自由。而我由衷同意。不斷復發讓我習於透過閱讀去滿足對知識的渴望,多瞭解一點點,會不會就更能夠理解自己與他人?精神分析學派也好、精神生物學派也罷,你該如何醫治人類的心靈?心靈是可以被現代科學醫治的嗎?
我們如何理解憂鬱症,將投射出社會對憂鬱症的宣判與解讀。
從歷史、政治、族群、生物性、社會環境等各角度拆解,可以一窺憂鬱症的部分樣貌:哪些儀式性讓病人願意進入社會醫療體系?科學與醫學的「大腦時代」正在往什麼方向走,意味著研究經費獲取與政治遊說的可能性,而這當中又存在著藥廠的獲利計算,我們該將人命放置於天秤的哪邊?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藥物,劑量是合理的嗎?成癮性該如何解?
憂鬱症患者所服用的藥物基本上是立基於現代醫學與生物學的詮釋,現行理想療法通常是藥物與談話治療(諮商)並行。但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負擔諮商,以台灣來說,諮商資源雖然不至匱乏,但也說不上豐富,更是所費不貲;因此在身心科入健保的前提之下,多數人當然優先選擇服用藥物。藥物成癮性與依賴性一直為人詬病,常見的臆測「西藥傷身」觀點(不論是否立論正確)在患者身邊的親友對談儼然已成標配,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更是令人避之唯恐不及。
自然療法(運動)或是另類療法(中醫)等規勸自行停藥的說法大行其道,不過,以腦科學的研究來看,藥物運作的原理是刺激或平衡大腦特定區域功能,讓特定傳導物質維持平衡,進而平穩患者情緒與降低干擾;若自行停藥,等於放任傳導物質失衡,反而可能提高憂鬱症再度復發的機會;而長期反覆的後果,則是在未來可能增加腦部產生病變的風險。
另外,在政治篇中提到,因為對腦科學的知識有限,造成藥廠與研究機構願意投注在憂鬱症研究的資源,與開發其他藥物能夠獲得的利潤有所拉扯,導致研究與開發因獲利或評估不足無法推進更進步或創新的研究。醫療與科學研究同時間也影響著遊說團體與智庫,而智庫則與政策制定環環相扣,進而直接影響醫療資源如何分配、以及社會如何看待身心疾病。政策搖擺與資源分配,將讓最有醫療需求的群眾受到最直接且最嚴重的傷害。
我們已經擁有足夠資料確認身心疾病與社會環境脫離不了關係,其緊密性超越新自由主義或個人主義的願意承認的程度。「都是個人的責任」聽起來既高貴又輕鬆,彷彿疾病是個人心智的缺乏與軟弱,此看法不僅在作者所在地美國、在台灣也比比皆是。社會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污名化、偏見與獵巫:在重大社會事件發生時,這些沒有發聲管道卻受著苦的人們往往最先被拿來興師問罪,人們則自傲地認為自己正揮舞正義的大旗。你看不見受苦的人,不是因為你有多高貴或努力,只是因為你還幸運而已。
我還活著。當憂鬱症回來的時候,每天早上睜眼,第一個浮出的通常是這句話。
今天不是新的一天,但我還活著。並不是多麽頑強抵抗自毀欲望的人,也不是什麼將生命捧入最高道德殿堂的人,只是單純的存在並等待著,等待必須被感受的存在本身,憂鬱與否。活著意味著有機會正面迎擊,活著也可以是在需要的時候任性地逃避喘息,活著就是可以在打開家門時看到貓用身體說愛,活著就是願意對生命中微小的瞬間感到心碎或感激,活著就是還願意相信。
相信在片段與片段的時間軸中,我有能力安放自己,面對下一次可能會來或不會來的陰影,相信在所有事情發生、所有疤痕纏繞的軀體上,或許有人還願意聆聽。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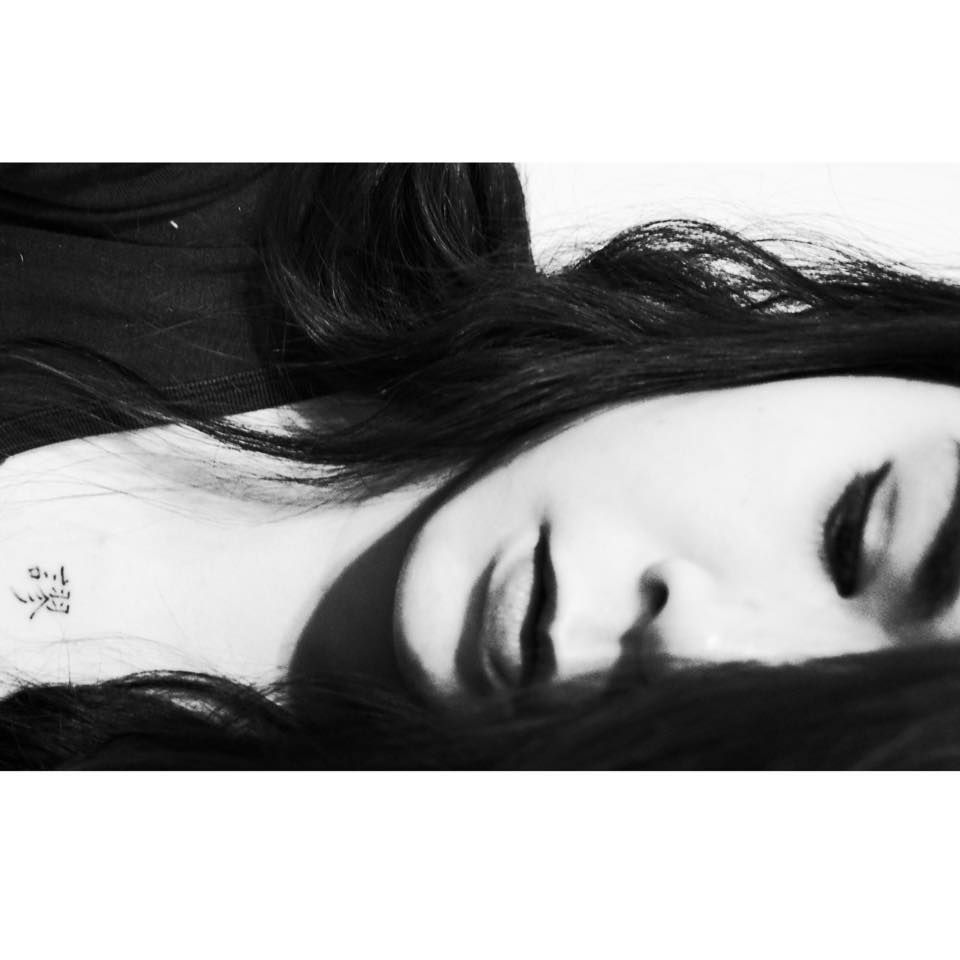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