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儿学习会之“更衣室迷思”:到底被看的是谁,被警告的是谁——女同包括跨女同是否果真是“拥有凝视权力的人”?
在三个副标题中难以取舍,最后选择了以上这个,另两个如下
・为什么女性主义需要跨性别
・我为什么恐惧“女性空间”
1,迷思的起点:事例分享,“女性性指向”的可视化恐惧?
在一次以跨性别议题为主题的讲演会中,有一位听众分享了她曾经在职场中遇到的真实案例:她的上司是一位MtF的跨性别女性,后来正式出柜并更改了姓名。这位上司的性取向是女性,伴侣也是女性。她提出希望从原本使用的男性更衣室改为女性更衣室,公司也同意了她的请求。然而,这个变动引发了部分女性同事的不安与抵触。理由是:和一位性倾向为女性的人共用更衣空间,会让人感到不舒服。
这位听众在分享中表达道:“我认为,确实有女性可能会对和性倾向为女性的人共用空间感到心理压力。为了让跨性别者与其他人都能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相处,设置单独更衣室或私人更衣间等设施,来营造良好的职场环境,是值得采纳的方式。我听说现在确实有这样的设置后,也感到十分认同。”她还补充道:厕所方面已经逐渐普及了无性别厕所,希望更衣室等其他设备也能尽快跟进。为了让各种性别与性取向的当事者能够感受到友善环境,我们有必要不加以“审查”地汲取他们的实际需求。
表面上,这似乎是一段“平衡双方立场”的发言,实则却暴露出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究竟是谁被视为“可能引发不适的人”?又是谁被默认“应该退让的一方”?“不安”的来源,并非纯粹的个人经验,而是社会长期构建下的性别与性取向想象。尤其是,“性取向=潜在凝视=不安全”的逻辑,既投射在跨性别女性身上,也波及女同性恋、双性恋和酷儿女性。
我们是否意识到,那种“我不反对ta,但我不想和ta共用空间”的说法,在维持表面宽容的同时,也在制度上制造了实际性的排斥?所谓“设置单独更衣室”的建议,其实是在把“不同”标记为“必须被隔离”的对象。
2,被凝视的恐惧,还是“凝视者”的假定?
当人们说“在同一更衣室会让人不安”,这种“不安”默认了一个前提:对方可能会以“性”的方式凝视自己,或“不是真正的女性”。不仅是对跨性别女性的怀疑(她是否“真的”是女性),更是一种投射:“她或许会用‘男性的方式’看待我们”。
作为女同志,我也经常在公共浴场或更衣室中感受到“必须藏起自己的身份”的压力。不是因为我真的在看别人,而是因为我可能“被当作那种会看的人”。凝视与否,不再是行为的问题,而是身份的“潜在嫌疑”。
没有人因为真实地凝视他人身体而被系统性地警告。被回避和排斥的,是“你不够女人”或“你喜欢女人”这类身份。而这套逻辑,不只针对跨性别女性,也指向女同志、双性恋女性和酷儿女性。
“女性空间”的准入条件,似乎悄然设定了这样的秩序:你必须是顺性别、异性恋、非威胁性的存在,才能被默认“无害”。这样的空间,真的安全吗?又安全的是谁?
3,看似中立的“个室”提案,是谁在被驱逐?
“设置单独更衣室”听起来好像体贴入微、兼顾各方,其实却隐藏着更深的结构暴力:谁必须退出?谁必须为“大家的舒适”而被隔离?
“大家”并非中立,而是被主流定义的“多数女性”。当权力结构认定“你不让人舒服”,你就要被请出去,那么“个室”就是一张驱逐令,只是换上了“理解与调和”的语气包装。
我们这些酷儿女性、跨儿、边缘性别者,也常常在试图“证明自己无害”。我们学会控制目光,避免身体接触,收起表达欲望的权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但我们真的拥有“凝视者”的位置吗?还是,我们才是被长期当作“凝视风险”、被系统性审查和排斥的那一方?
4,安全的“女性空间”,是谁的安全?谁在定义“安全”?我为何“恐惧女性空间”
当“女性空间”的安全只由主流女性来定义,只保护顺性别异性恋女性的边界时,它其实已经排除了酷儿女性、跨性别女性、女同志的主体资格。这不是安全,而是权力划分;不是调和,而是驱逐;不是善意,而是制度性的定罪。
讲演结束时,我脑中反复浮现的问题是:
当我们谈“女性空间的安全”时,我们在谈的是“哪一类女性”的安全?TERF所说的“纯女空间”,指的是“某种女性”的安全,而不是所有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让我们感到不安的那些人”,这种不安其实是结构性问题,其实并不是出于对方真实行为的警觉,而是出于社会不断灌输的“她们不是真正的女人”这一偏见。
“更衣室”不是一场关于行为的战争,而是一场关于边界、想象与恐惧的结构战争。而我们必须回到那个最基础的提问中:到底被看的是谁?又到底被警告的是谁?
5,存在即原罪,我们不需犯错就已被定罪
最近我持续关注跨性别议题,也重新思考“同性恋”这个身份。在不断交叉的经验与倾听中,我开始意识到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作为少数者,你无需实际做错什么。你的存在本身,就已经被视为一种“越界”。你无需触碰任何禁忌——你只是“在那里”,系统就已经开始寻找规训与惩罚你的方式。
你用不着实际犯罪——你本身就已经被系统判定为sinner。你开口说一个字,都是在给系统为你定罪的理由:当你试图解释、辩护、说出自己的立场时,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你是个问题”的社会认定。
这个系统总有办法重新确认自己的正当性——你越解释,它越坚信你是个问题,压迫少数者的方式会随着你的每一次发声而自动升级。
6,总结,所以我们(女同,跨儿)是否果真是“拥有凝视的人”?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根本问题,就会发现:
一、社会的“眼光结构”常常是这样运作的: “你的性倾向是女性 → 你可能会‘看’其他女性 → 其他女性会不安”。这其实是把“谁对谁有欲望”的想象,变成了一种“危险的征兆”,以此来监控边缘者的存在。
这种想象把女同志或跨性别女性,定位成“拥有目光=潜在加害性”的存在。
二、然而现实中,真正“凝视”的权力从不属于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才是那个被系统性“凝视”的人: 我们在更衣室中小心翼翼,不让别人误会; 我们在公共空间注意自己的举止与衣着,怕别人多想; 我们时刻被“作为凝视者”的想象所规训,却无法真正地说出自己的欲望。
所以,酷儿女性、跨儿、边缘性别者早已被卷入了结构性的陷阱。
我们努力“证明自己无害”,不去看别人,不敢有身体感知,不敢表达欲望,甚至开始反过来警惕自己。
我们被当作“拥有凝视权力的一方”,但其实始终作为“被凝视者”而活在社会的规范与监控之下。
我们被怀疑为欲望的主体,却没有表达欲望的自由。
这正是“酷儿女性/女同志/跨儿”这些身份所共同承受的深层压迫:你从未做错任何事,却被制度预设为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这不是你的错。我们必须清楚知道,这是制度性的定罪逻辑。
写下这些,正是为了抵抗在沉默中被反复宣判。
所以我们必须抵抗——不仅是为我们自己,也是为了重新定义“女性空间”的边界与构成。
女性主义若真要成为反压迫的实践,它必须回应这些现实中发生的排斥机制,必须站在那些持续被误解、被排除、被噤声的人的立场上。
再强调多少遍都不为过: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对“跨性别”的结构性压迫,就会知道,女性主义不仅需要跨性别,更必须与跨性别者共同重塑解放的可能性。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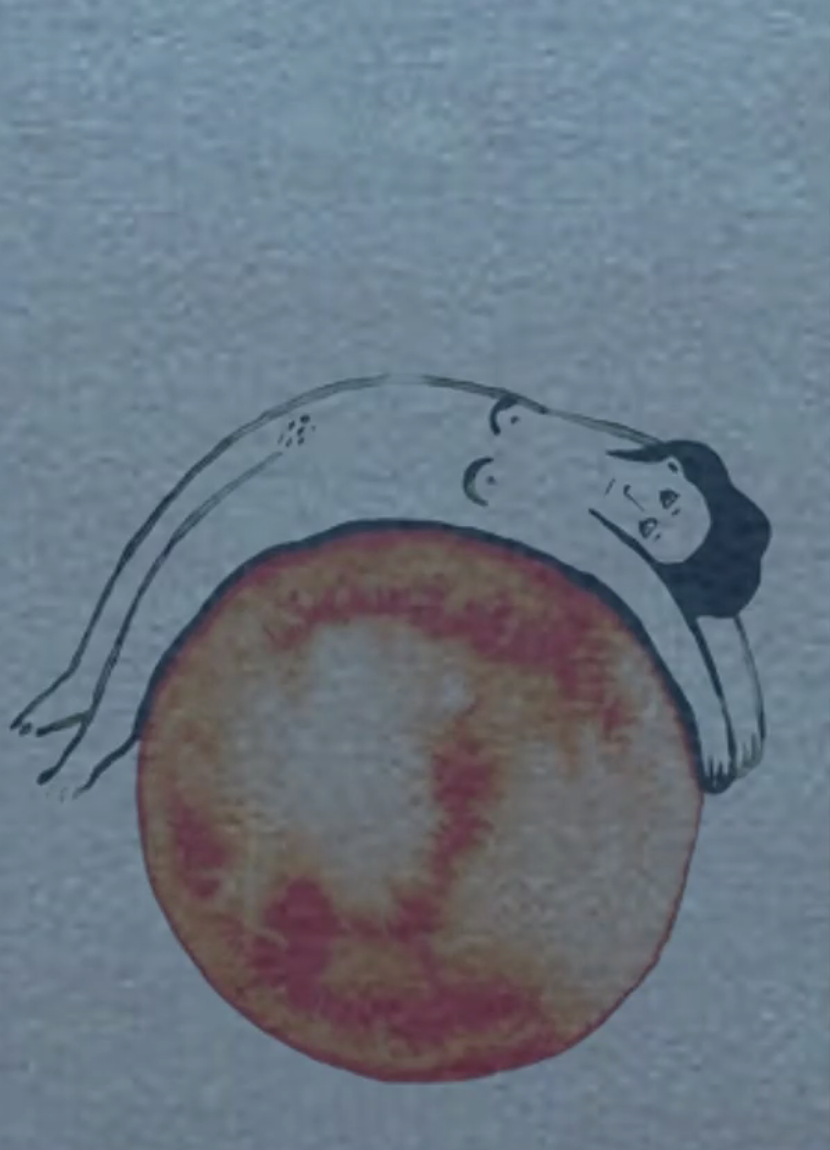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