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女同恋爱”是谁制造的幻觉?
1,谁定义了“什么才是女同恋爱”?
这段日子,在xhs和微博上看到了类似于:
・「女同性恋是两个女的在谈,不是一个长得像男人的女的和一个女的谈」
・「女同应该只喜欢女性特质浓的女生,不理解喜欢T的女同,和长得像男人、只做top的T谈,和男人谈有什么区别?」
一个长得像男人的女的和一个女的谈,就不是两个女的谈了吗?
和没有“女性特质”的女生谈,就是偏离了“女同”的“本质”——女性气质的相互碰撞?
我认为,将女同性恋锁定为“两个‘看上去很女的’女性在谈恋爱”,是一种同性恋内部的反向规训。本质是父权制性别规范的复制。
这些话语的共同点是:把女同性恋的“正当性”建立在外表性别气质的判断上。
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区分,而是一种父权制规训的内化与反向投射。
2,反向规训=被压迫者如何学会压迫自己人。
本来女同性恋就是两个女性相爱,不应该在意谁长得像男人谁长得像女人。
但如果硬要规定“女同性恋就应该是两个很女性化的人”,
就是拿社会(父权)教给我们的“怎样才算女人”的标准,反过来套在自己人头上。
被父权制洗脑了以后,把别人的规矩拿回来绑自己人。
这不是“纯粹女同”的守门,而是对“女性气质”的再规训、再评价。
3,被父权剧本洗脑的表现:
其实被父权剧本洗脑的表现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比如:
把外表的女性气质当成“好女性”的标准——
觉得“女生就应该长发、温柔、穿裙子”,否则就“不像女人”。
用“女生就应该懂事体贴”来要求自己或别的女性——
在关系里一味忍让、觉得自己不能生气,生气就是“不够温柔”。
在女同性恋群体内部排斥不够“女性化”的人——
觉得T、铁T、“长得像男的”就“不是真正的女生”、“不是真正的拉拉”。
etc
4,“厌T”与“厌男”的错位批判
许多关于“反T”或“厌男”现象中,男性特质(masculinity)的批判实际上搞错了敌人。
男性特质本身并没有原罪,力量、果断、独立、果敢、理性这些“阳刚特质”本身是中性的,它们本可以属于任何性别。
但是,当父权制垄断这些气质并用来支配,就变成了压迫的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毒男子气概”:
即,“如果你没有这些,那你就不是个男人,(是我们’推崇‘的)”的逻辑,其实和
”如果你有这些,那你就是’男人‘,(是我们’抵制‘的)“两种逻辑如出一辙,互为里表。
所以真正需要批判的是,父权制如何垄断、歪曲并把这些特质用来支配他人、压迫女性和非顺性别者。
如果只是一味厌恶一切“看起来像男性/阳刚”的表现,而不把批判指向父权制本身, 那么这种“厌男”其实只是另一个形式的父权逻辑:
——仍然被性别二元和权力逻辑所操控,只是反过来走向排斥与分裂,而不是解放。
真正的批判,不是讨厌“男性特质”,而是打破父权制如何规定和武器化这些特质。
真正的解放,不是反过来压迫男性特质,而是拒绝性别剧本的正当性,让任何性别的人都能自由地拥有、表达各种特质。
5,创伤+幻想:理想化的“纯女性性别空间”如何形成?
许多女同成员,经历过父权制下被阳刚气质、暴力、压迫性男性伤害的创伤。因为受过压迫,于是渴望一个“只有柔和、没有污染”的纯粹亲密关系。
在这种情感背景下, “女性之间的恋爱应该纯净、温柔、没有‘男性性别气质’污染" 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安全幻想。
因此,对“长得像男人的女同“产生排斥感, 本质上是创伤反应和理想化期待叠加的结果——背后所反映的是对完全脱离阳刚压迫气质的亲密关系的渴望。
但理想化不是问题本身,问题是是否愿意质疑这种理想化是不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6,在问:我们纯粹吗?之前,先问:‘纯粹’是怎样被塑造的?
父权制主导的文化中,恋爱被设定为一对性别气质互补的组合:一个主动、强势、阳刚;一个温柔、柔顺、阴柔。
这种“阳刚+阴柔”的剧本被默认为是“完整”“协调”“像样”的亲密关系。
这种想象深入人心,比如,当看到一对女同中有一方比较阳刚(T、铁T),
下意识地觉得她们是在“复制异性恋模式”,于是产生反感:认为“不够纯粹”。
但问题是:判断“像异性恋”,是因为已经默认“阳刚=男性/阴柔=女性”的剧本;
已经把“谁负责保护/谁负责撒娇”这样的分工,视作检验一段关系“是不是复制异性恋”的标准。
也就是说——以为在批判TPL复刻异性恋模式,实际上仍然在用“气质→性别角色”这种异性恋中心逻辑来评判同性关系。
“反T”没有跳出异性恋中心,只是用“看上去不够女”的那一方(T)来当替罪羊罢了。
女同关系不是“复制”了异性恋,而是被异性恋的模板拿来定义了。
综上所述,在接下来的道路上,关于“女同如何恋爱”这个问题我想我将持续思考,
尽管如此,我观察到中国拉圈大部分声音都是关于“女同‘应该’如何恋爱”——
“应该”这个字眼所代表的就是父权。女同恋爱不需要父权式标准。
女同不需要“女的像女、男的像男”的互补结构,也不必将自己的正当性建立于纯粹照搬任何视觉性别气质的剧本,
真正的解放,是任何性别都可以自由展现自己的特质,而不被“你像不像女人”所限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父权制最核心的机制不是单纯地让男性压迫女性,而是——通过制造和强化统治与被统治、中心与边缘、优越与劣等这样的二元秩序(“有力的支配者 vs 被支配的弱者”,“敌 vs 我”) ,来维护整体的社会控制。
所以,如果只是把现有的压迫结构反过来:“因为男性压迫了我,所以我要反过来痛恨男性”,那么实际上仍然承认了这种二元结构的正当性,只是想在旧秩序里换一个位置,而不是彻底拒绝这套游戏规则。
女同女性主义(lesfem)、反本质主义、交叉性社会主义立场下的解放,不是反过来仇恨男性,而是拒绝整个性别统治结构本身(划重点)
打破支配关系,让一切性别的人都能不受性别剧本束缚地生活和爱。
“性别气质≠性别身份=表演结果”,来自《Gender Trouble》(1990)“gender performativity”
“‘纯粹女同恋爱’是强制异性恋逻辑误导”,来自 Adrienne Rich《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強制的異性愛とレズビアン存在)》(1980)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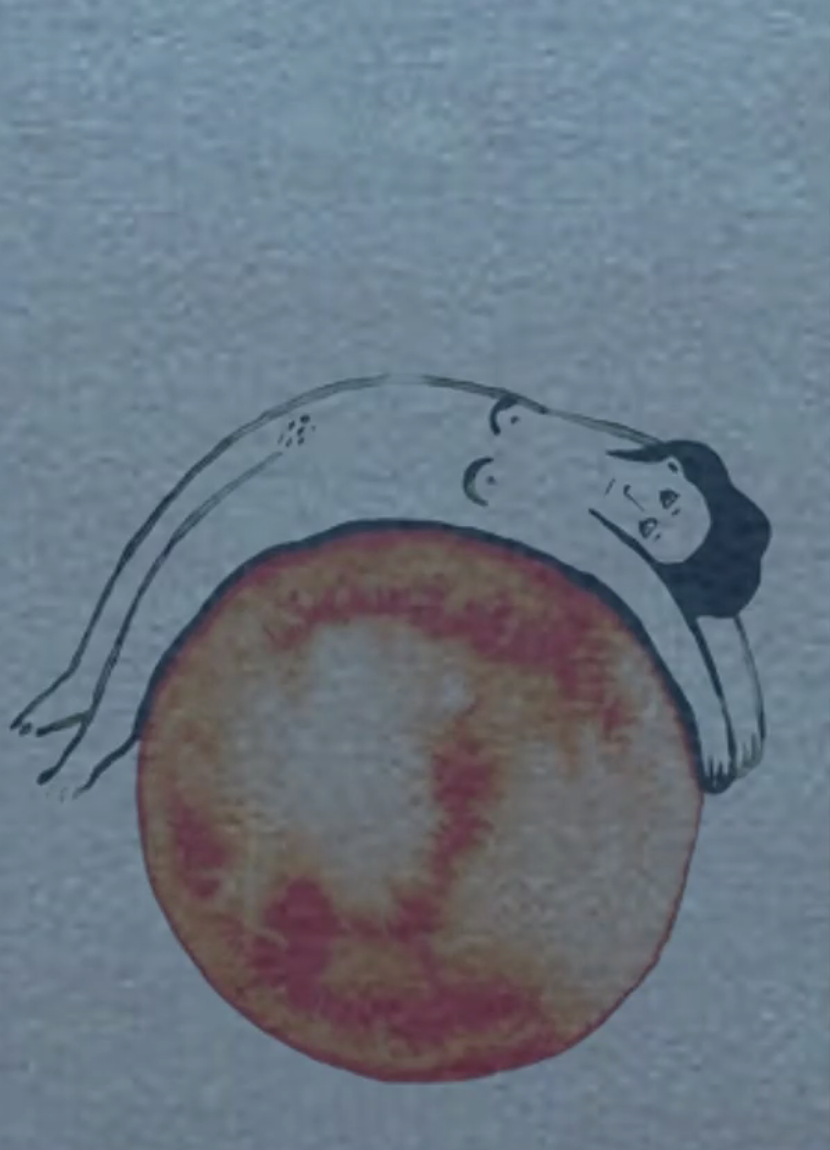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