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排外主义”/“xenophobe”
序:提问,总是会回到自己身上
今天看到清末爱砂老师的一条threads:
排外主义就存在于我们脚下。回头反思非常重要。排外主义者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是排外主义者。”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我对自由派左翼内部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排外主义感到危机。“是啊,那真的很危险”地附和着,同时又觉得排外主义和自己无关,于是那些话里本就含有排外要素的言论也就不知不觉被接受了。对自由派左翼政党的发言和视频也常常毫无批判地接受,结果就是对排外主义的共谋。排外主义就是这样,一天天被悄然生产出来的。如果现在不有意识地阻止它,就太迟了。
读完之后,我心里想,是啊,确实如此。我感受到这并不只是某种对ta人的批评,也是向“我这边”投来的质问。不是假设存在某种“排外主义者”然后就此结束,而是去意识到,自己也可能嵌套在那个结构里。那种内心微微发涩的不适感,也许正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被这个提问所指向——换句话说,排外主义并不是属于“某些人”的问题,也不是“那些人”的问题,而是也许“我”体内也存在着的东西。
1. 也许我是加害者:你真的从不歧视别人吗?
我一直有种感觉:大家都觉得“我绝不会歧视别人”。当人们特定地指责某些人说“那样的人真的很糟糕”时,其实是在肯定“我不是那样的”“我绝对不会做那种事”。换句话说,这种态度的背后,是对自身“正确性”的某种确认机制。当我察觉到责备ta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对自我正当性的欲望时,我就更想把注意力投向背后的结构,而不是轻易地将一切怪罪于某个人身上。
1-1. 在这个人人想当受害者的社会里,我们还承认自己是加害者吗?
这个社会里受害者意识正在蔓延。整个人类社会似乎都笼罩着“我被剥夺了什么”的失落感(这个问题在左右派中都存在,但这里暂且不展开)。经济不景气、政治保守化、勉强维持心理平衡的生活……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好像更想站在“被伤害的一方”。
或许,诉说着“look what society did to me,你看社会对我做了什么”,正是人们试图守护自己内心的疼痛、愤怒和不安的方式,因为尊严和情绪都岌岌可危,“我是受害者”的说法成了一种心理防御。在这样的氛围下,如果有人感觉“我是受害者”,那要他们思考“我是否也可能成为加害者”确实会很困难。
我一直觉得,那些说“我绝不会犯罪,我绝不会伤害人”的人,非常不可思议(不是讽刺,是认真的)。因为我几乎从来没有这种自信。我一直都和“也许我就是加害者”的感觉共生而活。为了保护自己内心的什么,或者在无意识中,我也可能会将某人排除在外——我深知这种可能性。
1-2. 正因为拥有特权,所以无法“无关”
从不认为自己和歧视毫无关系,还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有多大权力”,而是因为“有特权”。比如,四肢健全,经济状况相对稳定,作为独生女在一个算是富裕的家庭长大,能在日本长时间生活并顺畅沟通。这些条件无形中将我置于“内部”的位置。让我意识到我其实并不是“局外人”。
2. 是“界线”在制造歧视:跨界与排斥——质问父权制的逻辑
2-1. “内”与“外”的界线 ——越界者为何总被视为“违规”?
歧视和排外主义,总是从划分“内外”开始。谁在这一边,谁在那一边——我们通过画出这条界线,来获得某种安心。但这条线几乎总是在“看似保护某些人”的同时,“实际排除另一些人”。
我思考了各种形式的“界线(或者说边界)”:顺性别与跨性别、异性恋与同性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界、外国人与日本人……我们到底以什么标准来区分?这条线到底划在哪?——每一次划线,都是将某些人放进“内部”,而另一些人置于“外部”。我认为,这种划界的行为,正是父权制所擅长并不断复制的逻辑。
而那些试图跨越界线的人——比如跨越性别的人、在异性恋框架外选择爱的人、试图越过国界生存的人——往往会被嘲笑、惩罚、或被当作不存在。父权制将界线之内视为秩序,而把越界者当作“不稳定的存在”,试图将其排除。所以,越界总是被当作“违规”。
2-2. 当“安心”与“正义”成为排除的工具
在父权制统治的社会中,我们早已内化了以下判断方式:谁是自己人,谁是异类;谁可以被欢迎,谁需要被怀疑。我们在情绪与判断的深处早已染上了这种区分方式。“安全”“安心”这些词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打算排除谁?当我们保护什么的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在舍弃什么。
歧视,终究也是一种“划线行为”。谁才是“合适的”?谁是“正常的”?这些判断遍布制度、媒体和日常语言中,而我们正是借由顺应这些判断,来试图站在“正义”和“安心”的那一边。但在这种安心当中,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什么都更让人害怕。
2-3. 歧视是结构性问题,并且是交叉性的
父权制,为了守护秩序,总是试图划分“正常”与“越轨”。谁能被当作“家人”,谁会被当作“外人”?谁是“正当的”,谁是“越轨者”?这种划线的逻辑,已经悄然被植入我们的日常判断与感受中。“安心”“正义”的背后,往往藏着“對於’排除‘的許可和默認”的权力。
此外,歧视绝不是某个人的偏见,而是社会为了维持“秩序”所建立起来的结构性机制。它决定谁承担什么角色,谁应处于哪个位置。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出的那样,这种机制与劳动与再生产中的剥削密切相关。而交叉性视角则揭示出:性别、阶级、国籍、残障、居留资格等差异叠加之时,谁最终会被置于“最被排除”的位置。这些结构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如同地表一样,彼此连缀、共同作用在我们脚下。
3. 作为酷儿而活:我就是“提问”与“抗争”的结合体
3-1. 什么是酷儿:超越二元对立,质疑边界的生活方式
我是一个酷儿。
酷儿这种生活方式,看我看來,一直在与这种“划界”的方式抗争。它不仅是不顺从固定的性别分类与规范,更是在质疑“划界線”本身、动摇邊界、超越邊界之间主动选择而生的一种存在方式。男/女、异性恋/同性恋、健全/残障、正常/异常。那些无法被任何一对二元划分所收编的存在,就是酷儿。酷儿拥有打破界线的力量。它像是在已被划定的框架中,插入一句“真的是这样吗?”的噪音,更是一种反边界(anti-border)的实践方式。
所以,对我而言,作为酷儿,活在酷儿之中,既是对歧视与排外主义的反抗,同时也是对“内”与“外”这种秩序——也就是制造歧视的父权逻辑本身——的抗议。酷儿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抵抗界线、搅乱界线、发出质问。
4. 反结构主义:因为我们不可能无关
4-1. “反结构却在加担结构”的矛盾:从“再生产结构的自己”开始出发
过去半年,我确立了自己“反结构”的立场。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必须直面那个“被结构铭刻的自己”。即便你自认为在反对结构,却无法逃避你自己就在结构之中——站在反结构的立场上之后,这样的感受一次又一次地击中我。越是想要否定结构,越不想承认自己正在加担结构。但这,正是结构的可怕之处,也是所谓“结构再生产”的本质。连“反结构”的姿态,某些时候也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复刻结构。
我并不想宣称自己和歧视、排外主义无关。因为,“我想无关”这种愿望本身,就已经有否认结构共谋、进而再生产它的危险。恰恰是“我不相关”这种姿态,才是在结构内部最狡猾地重演排除机制的方式之一。即使我处在批判歧视与排外主义的立场,也仍然拥有着在结构中的某些特权。正因如此,我无法说出“我无关”。如果真的要批判歧视与排外主义,那就必须从“我也是可以再生产这些结构的人”这个意识开始。
小结:不是“远方的他人”,而是从自己的脚下出发
我们所反对的,往往也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歧视、排除、厌女症,甚至如果不叫“犹太复国主义”,也可能存在着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凝视——如果没有这些意识,歧视与排除就会不知不觉被当作“和自己无关的远方之事”来处理。
我想,真正的连带不是无辜的宣称,而是从承担自己的共谋性开始。因此,我希望今天也能怀着对自身的怀疑活下去。想在试图划线的那只手、在想保护自己却因此而伤害他人的那个瞬间,察觉自己的动作。我不想放弃这种察觉的感受,也希望自己始终具备那样的敏锐。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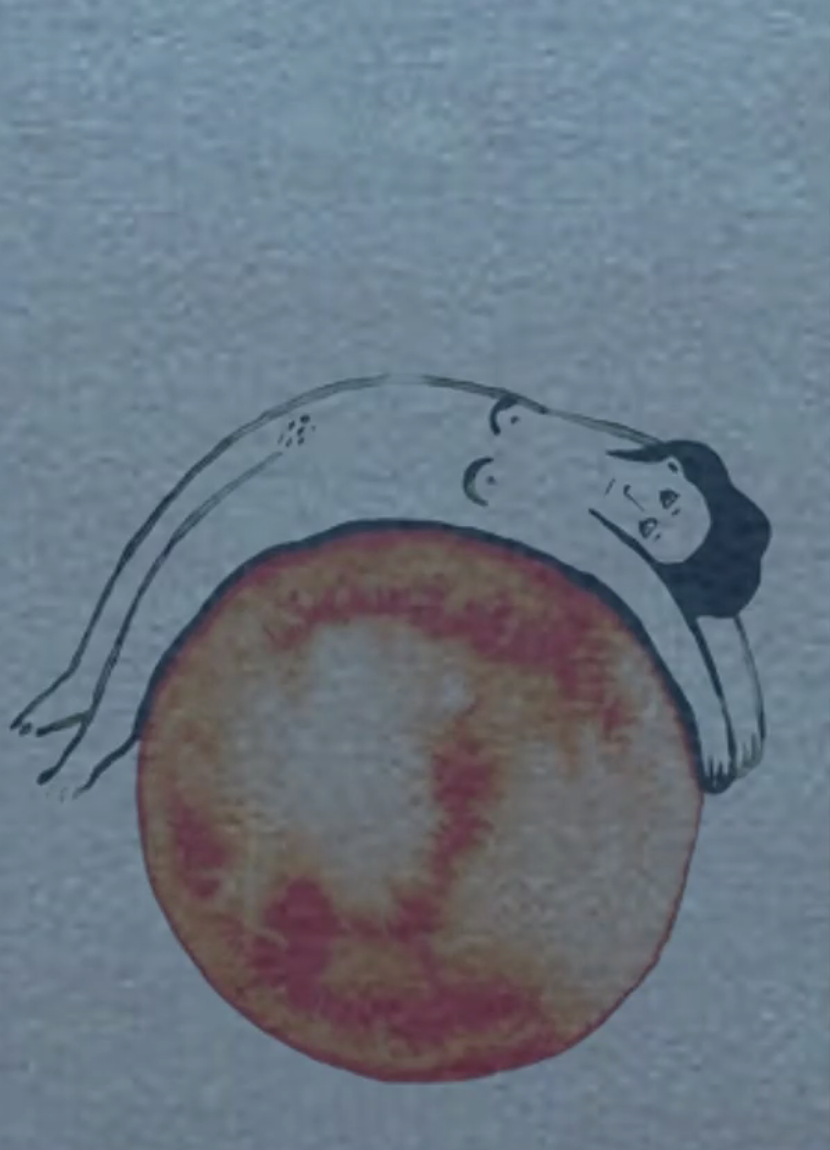
- 来自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