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同性伴侣登记制难产:Ta们不能“合法”参与伴侣的生老病死
作者:何文庭

71票反对、14票赞成、1票弃权。9月10日,仅承认最低限度民事结合权利的《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条例草案》(下称“草案”),在香港立法会恢复二读辩论后被否决,无法进入三读程序。这意味着,同性伴侣条例目前将无法正式立法,但受制于终审法院相关判决,香港政府表示会研究行政措施,但又强调《基本法》承认的唯一婚姻制度是异性恋。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此届建制派占90席中89席的香港立法会,首度否决政府提出的法案。建制派是相对亲特区政府、亲北京的政治阵营。
同性伴侣条例的推进,源起于“岑子杰案”。2018年,因港府不承认海外同性婚姻,与同性伴侣在美国结婚的“彩虹行动”成员、前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向高等法院提起司法复核,但原讼庭和上诉庭均败诉。2022年,岑子杰再度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2023年9月,终院裁定岑子杰终极上诉部分胜诉,要求香港政府在两年内,即2025年10月27日前,提出替代法律框架,承认同性伴侣关系,以满足性小众群体基本社会需求,以及获取合法身分认同。
然而两年来,港府迟迟未有跟进。今年7月2日突然向立法会建议立法增设“同性伴侣关系登记机制”,允许符合已在海外注册等6项条件的同性伴侣在港登记,享医院探视、参与医疗决定、处理身后事等权利。
港府公布的草案中,同性伴侣权利仅限于病、死相关事宜,然而即使如此,草案仍未获得香港立法会一读、二读的多数赞成票。
二读被否决后,同性伴侣权益案的当事人岑子杰形容,这“将会成为一道未愈合的伤口”。而香港首个由同性恋者创立的基督新教教会基恩之家则质疑,立法会在面对法院已确立的违宪判决时,责任并非辩论是否给予权利,而是制度如何落地。

意见书打开的世界:人们为什么同意,或反对?
二读前,香港政府曾忽然向公众征集书面意见。短短6天内,共收到10,775份意见书。根据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统计,支持草案的共有2081份 (19.3 ) ,其中705份来自同一份模板表格; 而表示反对的则共有8694份(80.7%)。
然而,官方统计数字背后另有文章。性/别小众倡议型媒体G点电视指出,政府并未提及反对方也有大量“模板式”意见书,甚至只是更改姓名及联络资料。 民间团体婚姻平权协会则分析表示,只有6成意见书可在立法会网站公开查阅,其中,约一半使用模板回复,主要反映特定团体的动员,而非广泛公众意见。
此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在2023年发布的调查显示,85%的香港市民认同同性伴侣应享有异性伴侣所拥有的部分权利; 60%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只有17%反对,23%中立,公众支持度比2013、2017年显著增加。
纵然充满“模版”争议,但公开的意见书仍打开了一个观看正反方民意的窗口。支持同性伴侣条例草案的意见书中,不少性小众讲述了他们的个人经历和生命故事,难产的条文对许多个体而言却是生活中处处掣肘的困境。
其中最受媒体关注的,是54岁丧偶男同志Kevin的故事。2021年,伴侣因抑郁症自杀,Kevin因“没有正式身份”,无法为其办理后事,男友亲戚也拒绝沟通安葬、遗产安排。也因此,“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都被剥夺”。
Kevin与男友相识于2008年,2012年开始同居。由于香港不承认海外同婚,到外地注册手续繁复、开支大,二人未到外国注册登记结婚。男友曾定立遗嘱,将同居居屋产权留给他,但没有向家人出柜。
居屋的产权纠纷、伴侣的死亡证明在不明原因下迟迟未发出,加之缺乏“合法身份”和未通知被更换了门锁,也导致他4年多无家可归。Kevin的护照、回乡证、财物衣物、银行卡,甚至曾经的纪念品、日用品等,均锁在无法回去的“家”中,直至今日无法打开。Kevin在自我陈述中写到:“我们只是两个很平凡的基佬,带着自己的软弱,想像自己会做得好一点,但仍然未能接得住彼此。”
公开的意见书里,也不乏知名人士。例如,知名画廊3812 Gallery共同创办人Mark Peaker写到,他在香港生活超过三十年,与港人伴侣一起经营艺廊,2023年6月,两人在新西兰登记结婚,但这份伴侣关系的承诺却“在这个我们称作‘家’的城市仍未被承认”。
从大陆来港等移民同性伴侣,也提到移民者的处境。来自广东省汕头的许任明写道,他与伴侣在大学认识,相爱8年,努力克服周围人的眼光,获得了父母支持。但他担心,若自己遇到紧急状况,老家父母要花至少5小时才能赶到香港。“我希望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最爱的人能在第一时间代表我签下字。”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关心LGBTQ权益的异性恋市民、开明基督徒、学生团体、NGO等写信表达支持。有人列出数十条参考资料链接,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小红书五棱镜同好群”提交的”红头文件“。
另一边,反对的意见书多来自持保守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和人士,理由是草案会影响传统婚姻制度、家庭价值、伦理关系、繁衍后代,甚至有人上升到危害国家安全层面。
香港同性伴侣权益:一桩桩法律诉讼的征途
在这份草案之前,香港同性伴侣的法律权益,主要是通过一桩桩诉讼逐步取得突破。不同的性小众个体,用个人经历的不同切口和判例,试图在普通法体系下撬开一道道缝隙。
其中一个关键里程碑是“QT案”。英籍女同志QT与伴侣在伦敦民事结合后,准备随伴侣一同移居香港,却被香港入境处拒绝签发受养人签证,因此于2014年提出司法复核(注:司法复核,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公共机构行为合法性审查)。历经四年三审,至2018年,香港终审法院判QT胜诉。此后,这一判例使得海外注册的同性配偶能以受养人身份留港。
更重要的是,“QT案”确立了“除非政府能提出公平和合理的理由,证明同性配偶不应享有某种权利,否则任何对同性配偶的差别对待都属歧视”的法律原则,这也是后来多宗同性配偶司法复核案的基础。
“梁镇罡案”是另一大标杆性案件。香港男同志公务员梁镇罡与伴侣在海外结婚后,公务员事务局拒绝向他的伴侣发放配偶福利,税务局也不允许二人合并报税,梁于是在2015年入禀高院。案件同样打至终院,耗时3年,梁镇罡一方最终完全胜诉。
自此,香港公务员的同性配偶可享有相关配偶福利,税局也更新了《税务条例》,在处理税务时将同性婚姻视为有效婚姻。终审法庭裁决中提到,同性配偶能否享有另一半的工作福利,与保护传统婚姻无关;而以“缺乏社会共识”为由剥夺性小众权利,是损害基本人权。“梁镇罡案”的这一法律原则也被后来其他同性婚姻平权案频繁引用。

事实上,就在同性伴侣条例草案被立法会否决的前一天,香港同志妈妈亲权案也取得了进展。
一对已在南非结婚的女同性伴侣R和B,在2021年以“互惠人工受孕”(Reciprocal IVF,俗称“A卵B怀”)方式生下男婴K,其中R提供卵子,B怀孕生产。她们尝试在香港登记为男婴的双亲(Parents),但只有B被列为法定母亲。两人在2022年入禀高院,要求法庭确认R在法律上的家长地位,法官于2023年驳回R的申请,仅宣告她在普通法原则下应该被承认为家长,但不能成为法定家长。同年,R作为监护人代表男婴再提起司法复核,挑战香港《父母与子女条例》和《生死登记条例》,要求确立她的法定母亲身份。今年9月9日,高院裁定,前述条例和香港政府做法违宪,构成歧视,具体处理方式有待诉讼各方进一步陈词商讨。
法庭在判词中写到,“父母”的刻板性别定型已不合时宜,家长的性倾向不一定对子女有负面影响,“双重母亲”本身根本不构成问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会阻碍孩子成长、建立身份认知。这一案件的成功,令今后香港同性伴侣通过“A卵B怀”生育孩子,双方与下一代的亲子关系都将获香港法律承认。
目前,同性伴侣或配偶在香港已拥有10项权利,包括参与医疗决定、继承遗产、处理丧葬事宜、以家庭单位入住政府资助房屋、申请成为无血缘子女的监护人、登记为“A卵B怀”子女的法定家长、享受公务员配偶福利、申请受养人签证、合并报税、成为人寿保险受益人。此外,同性配偶或同居情侣若受另一半家暴,可以申请强制令。
不过,诉讼的背后是消耗的资源战。面对司法复核起诉,香港政府几乎在每一次败诉后,都会动用庞大的法律、人力及财政资源不断上诉,直至到终院。
例如,争取同性配偶申请公屋权的Nick Infinger案,从2018年提诉,至2024年终院裁定政府败诉,历时长达6年。而同性配偶入住居屋、继承遗产案(吴翰林案)从2019年打到2024年,期间,吴翰林于2020年底因抑郁症自杀离世,伴侣李亦豪强忍悲痛接替他继续打官司,只为完成亡夫遗愿。历经5年,同性配偶以家庭成员身份入住居屋、继承另一半遗产的权利,最终等来法律上的承认。
在同性伴侣权益逐项拆解诉讼的同时,直接挑战核心婚姻制度的尝试却屡屡碰壁。与岑子杰案同年(2018年),还有另外两宗备受关注的同性婚权案——“MK案”与“TF案”。女同志MK、男同志TF分别提出司法复核,争取同性婚姻或民事结合合法化。高院原讼庭判前者败诉,当事人未再上诉;TF案延后至MK案完结后才处理,也没有下文。
岑子杰案的终审判决中,法庭裁定政府应提供承认同性关系的替代方法,但驳回剩余两条上诉,认为婚姻宪法自由只属于异性婚姻,香港政府不承认海外同性婚姻的做法并不违宪。
这反映,即便法院承认性小众需要某种保障,但一旦涉及婚姻的根本定义,便始终不愿动摇“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传统制度,《婚姻条例》、《婚姻制度改革条例》是它们不想触碰的禁区。
即使部分权利已获法律承认,缺乏婚姻制度保障的同性伴侣在现实中仍遇到重重阻碍。
平权倡议组织“萌家香港”今年5月至8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包括异性恋在内的96%港人认为于法律上承认伴侣关系有其重要性,但在有一名固定伴侣的LGBTQ+人士中,55%没有任何正式登记。 由于香港法制不承认LGBTQ+伴侣关系,LGBTQ+人士当中有接近七成难以享有配偶福利(69%),不能以家属身份接受社会服务或支持(67%),无法申请公共福利(66%)。42%的人在医疗探访遭遇困难,超过三成半在遗产承办(35%)以及处理身后事(36%)方面遭遇困难。
如同给旧制度“打补丁”的一件件司法复核胜利,虽然来之不易,却零散而被动,症结在于未能形成一个全面承认同性伴侣关系的法律框架,这也是岑子杰案要求香港政府从根本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意义所在。
后国安法时代,公开倡议寸步难行
同性伴侣替代框架的立法挫败与香港近年来的政治环境恶化密不可分。 过去,香港LGBTQ运动主要是通过游行、集会、公开倡议和社群动员来争取权益。
创办于1986年的香港首个LGBTQ组织“十分一会”,1988年发起一人一信行动,呼吁同性性行为非刑事化,这是香港性小众群体首次为争取平权公开发声。1991年,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修订,正式将同性性行为除罪化。此后,更多新兴LGBTQ团体注册成立,举办讲座、聚会,透过媒体、学界、议员发声,要求就性倾向设立反歧视条例。
千禧年的香港性小众运动进入街头。2004年,首次小规模同志游行有约百人参加;2005年起,又连续举办了四届“国际不再恐同日”香港区游行;至2008年12月,首次有了上千人参加的同志游行。随后的10年间,除了2010年因经费不足停办外,每年均持续举办,游行参与人数逐渐上升至万人,成为华语地区标志性同运活动之一。2014年,又从新加坡引入“Pink Dot”,以户外嘉年华形式呈现,曾在政府总部前的添马公园、西九苗圃公园等人群众多、位置显眼的露天场地举行,每年亦吸引超过万人参加。

然而随着香港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游行、集会的空间逐步缩小,甚至消失。
2019年反修例运动期间,香港警方拒绝主办团体的游行申请,香港同志游行改为集会,同年,Pink Dot亦停办。2020年7月,港区《国安法》生效,加之疫情影响;8月,Pink Dot 宣布转为网上直播;11月,警方以疫情持续、禁聚令仍生效为由,发出反对通知书,同志游行亦被迫以线上直播代替,自此再无游行与集会。2021、2022年,同志游行、Pink Dot 均改成室内市集。防疫限制放宽后的2023年、2024年,Pink Dot恢复在西九文化区的户外嘉年华。
不过,就在今年同性伴侣条例草案审议之际,Pink Dot 遭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突然拒租场地,被迫取消。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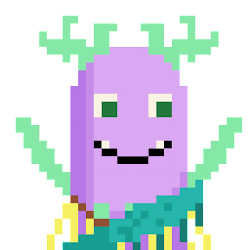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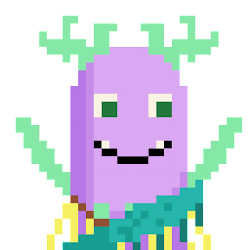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