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高傲與陷阱 :Christopher Lasch《菁英的反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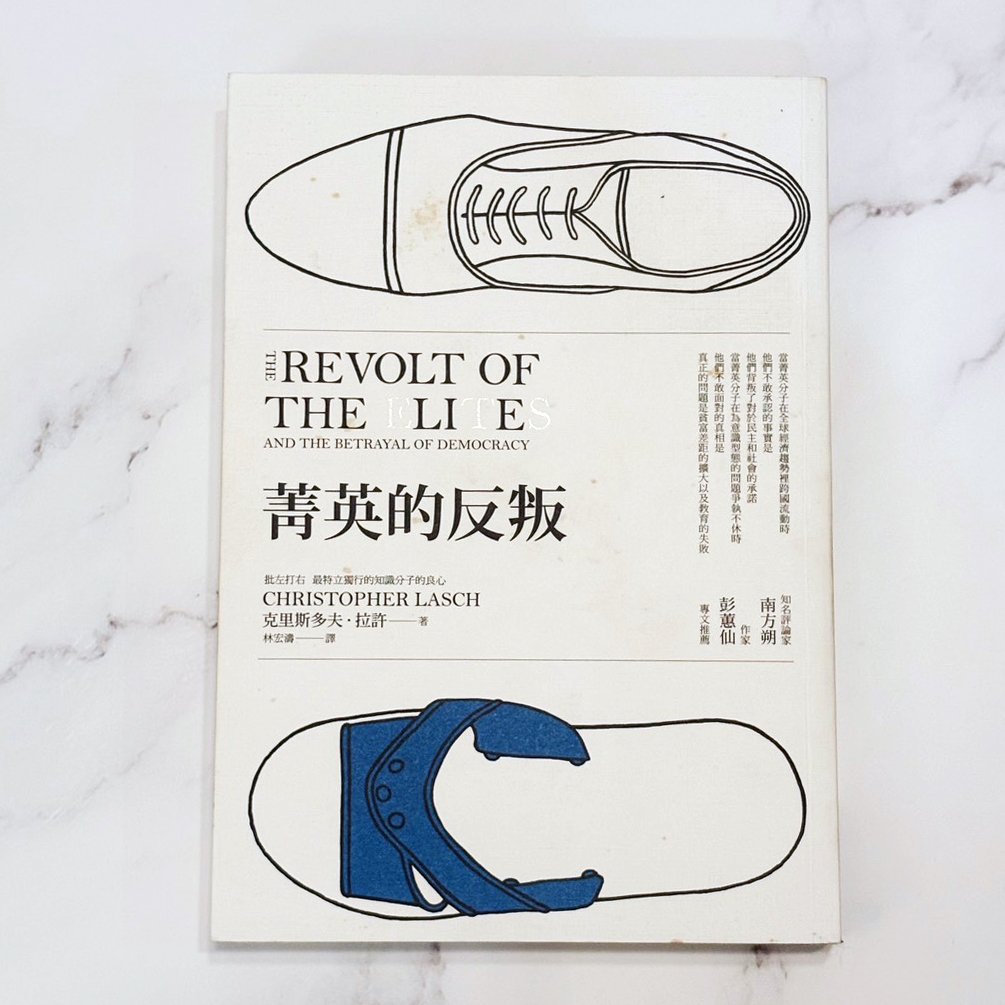
民主需要觀念和意見的針鋒相對。觀念和財產一樣,需要盡可能的普及流通。然而那些自認為「出類拔萃者」,總是懷疑一般公民是否有能力理解複雜的議題並提出批判。
在強權夾擊與公共理性失語的年代,究竟是再也不需要知識份子,還是更迫切的需要可以意識到展開對話空間之必要的知識份子?
埃莉諾 · 羅斯福於1948年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為人權而奮鬥》有名的一段話:「民主、自由、人權對世界人民而言已有明確的意涵,我們不能允許任何國家將其扭曲,使其與壓迫和獨裁劃上等號。」聽起來無比正確,但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必須重新詰問:何謂民主?如何實踐民主?
Lasch在《菁英的反叛》指出,當代知識份子若非叛逃,便已融入菁英體系之中,參與著一場與人民脫節、拒絕溝通的話語壟斷。知識階層的菁英化,造就了政治與公共論述場域的荒漠:民眾的語言能力與思考習慣被摧毀,僅剩符號化的立場歸類與意識形態選邊;而知識份子若非向階級鞏固的利益靠攏,不然就是淪為同溫層之間互相舔舐傷口。說實話,考量批判思考與對話空間的喪失,真的不難理解為何反智的民粹主義何以在當代橫行。
知識份子的反叛,在於拒絕承擔民主的真正責任。以「專業」為盾,築起溝通的高牆;以「進步」為名,執行階級資格審查制度。公共對話因此喪失彈性,政治辯論成為排擠異己的荒誕喜劇,應該要是建構民主基石的理解與協商,在全體或個人利益中被徹底遺忘。這個號稱言論最自由的時代,看到的現象卻荒唐至極:每個人都在發出聲音,但鮮少見人組織有意義的字句;每個人都在說話,但卻沒有人在溝通。
全球化信仰熱潮過後,媒體與人性催生了廣告發展歷史中最分眾的世代,無數小分眾與舒適圈泡泡,將人們凝聚在自己的群體不斷討伐異己,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提出的「他者」的概念從未如此幽微卻真槍實彈的在日常上演。當代社會媒體的分眾與演算法,更進一步讓群眾困在舒適圈中彼此廝殺。
人們碎裂為彼此敵視的島嶼群,在自己的泡泡裡構建真理,對外則充滿猜疑、誤解、與道德羞辱。這樣的環境下,溝通被視為示弱,理解被視為背叛。人們拒絕必然複雜的批判思考,只想要立場清楚、二元對立的快速結論。
知識份子的責任是什麼?若知識不為理解而存在,只為標籤與劃界,那我們還剩下什麼?民主若僅止於選票,或只是意見的累積與叫囂,那我們離集體沉默還有多少距離?無端謾罵、取笑,好一點的是自以為是的批判,更常見的是非人化的扭曲攻擊。我們與我們嘲笑光譜另一端的他者在行為上並無顯著不同。我們僅管彼此鄙視,沒有人想要溝通,沒有溝通就沒有理解可能,民主制度在此失去其解決問題的能力,甚或,只剩被極權收買的價碼。
有多少人在想到民主的時候,會把它當成幾乎只等義於可以投票的權利。但開放人民投票的極權政府比比皆是,甚至有些極權政府可以靠掌控媒體或操作恐懼,在不用做票的前提之下贏得選舉,那他們算民主嗎?還是被單一簡化為可以總統直選,票票等值?那沒有總統直選的國家算不算民主?
以現代定義而論,民主基石包括集會及言論自由、通訊自由、平等、公民權、選舉權、生命權,代表著主權在民,即「公民做主」。看起來都很對,我們都符合。但知識份子在這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我們的言論自由成為了在人人皆有權在網路上裸奔還沾沾自喜的笑話,通訊自由掌握在科技巨擘手中,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要自己不吃虧通常都不那麼在乎是否平等,公民權被為反對而反對濫用、選舉權變成用腳投票的惡夢。二十一世紀的知識份子,許多人都在叛逃:他們不再扎根於公共生活,不再相信人們有能力思考,只將人民視為操作對象,或者鄙視的愚民。於是這樣的傲慢,變相地提供民粹主義大行其道的柴火。
讀完此書後的我,從過去的在網路上與人筆鋒相對,到願意選擇與生活中的異溫層展開對話、試圖理解對方。我不再那麼執著辯論輸贏,我更在乎的是在我們談話的過程中是否可以先聚焦,把那些被濫用的大字一層一層剝開,試圖理解對方實際上想說卻沒說的究竟是什麼。雖然很多時候,多到令我難受,人們早已習慣了被媒體豢養,被權勢摸頭,人們耽溺於眼前的視覺垃圾,勝過遠方正在發生的尖叫與哭喊,而沉默,往往是極權最渴望的民眾特質。
若還願意重新認識中產階級知識份子的責任,意味著必須選擇真誠的溝通、選擇不說廢話、肯認他人痛苦、願意不斷拆解自己的確信與立場,並有勇氣承認自己也可能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唯有如此,我們才可能重新建立公共語言、才能讓民主恢復它作為公共協商機制的力量,而不是一場場充滿羞辱與退場的短兵相接。那些固執己見,其實都來自於對未知的恐懼與對思考的陌生,但那怕只要還願意相信人類的最大公約可能性,即是所謂生命與善,那所謂真正的、承襲歷史脈絡而來的、尚未叛逃的「知識份子」,或許就還有存在的理由。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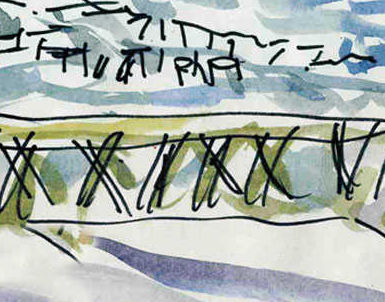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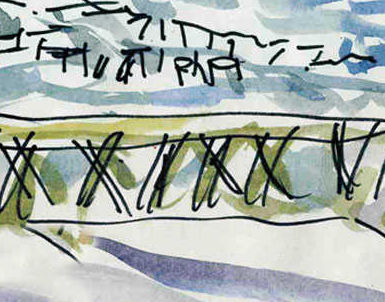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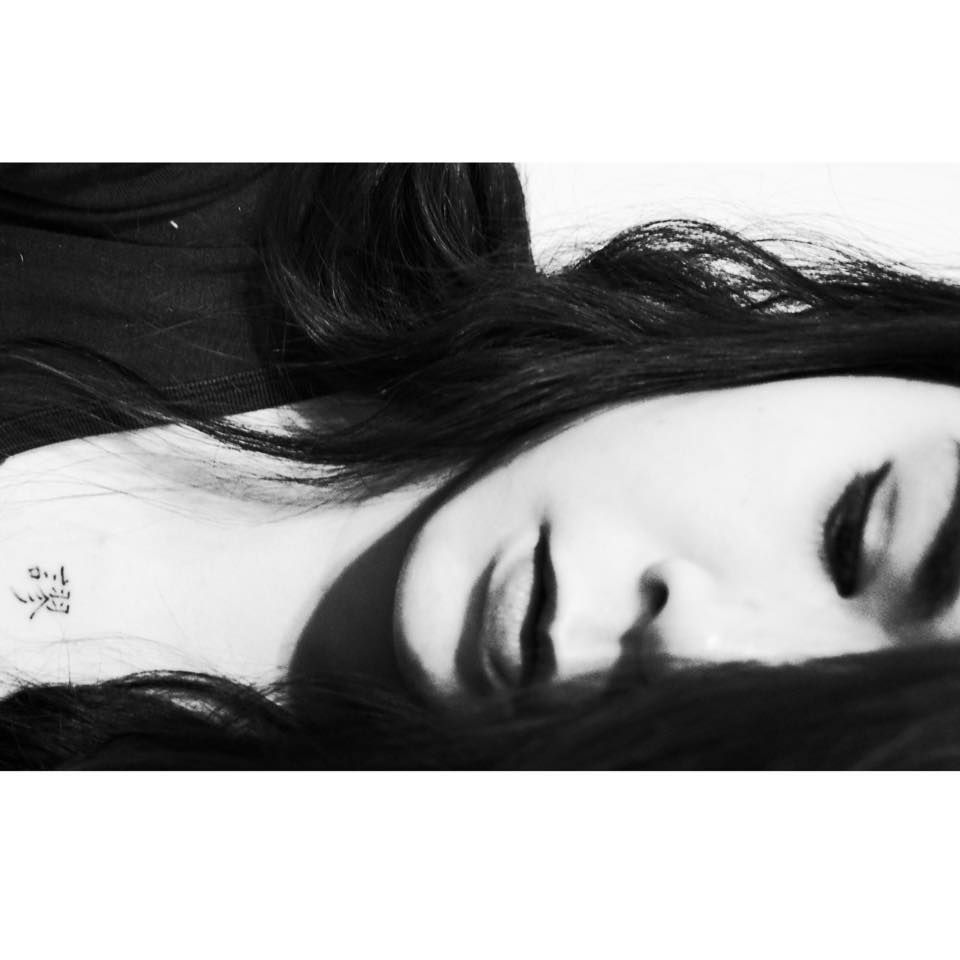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