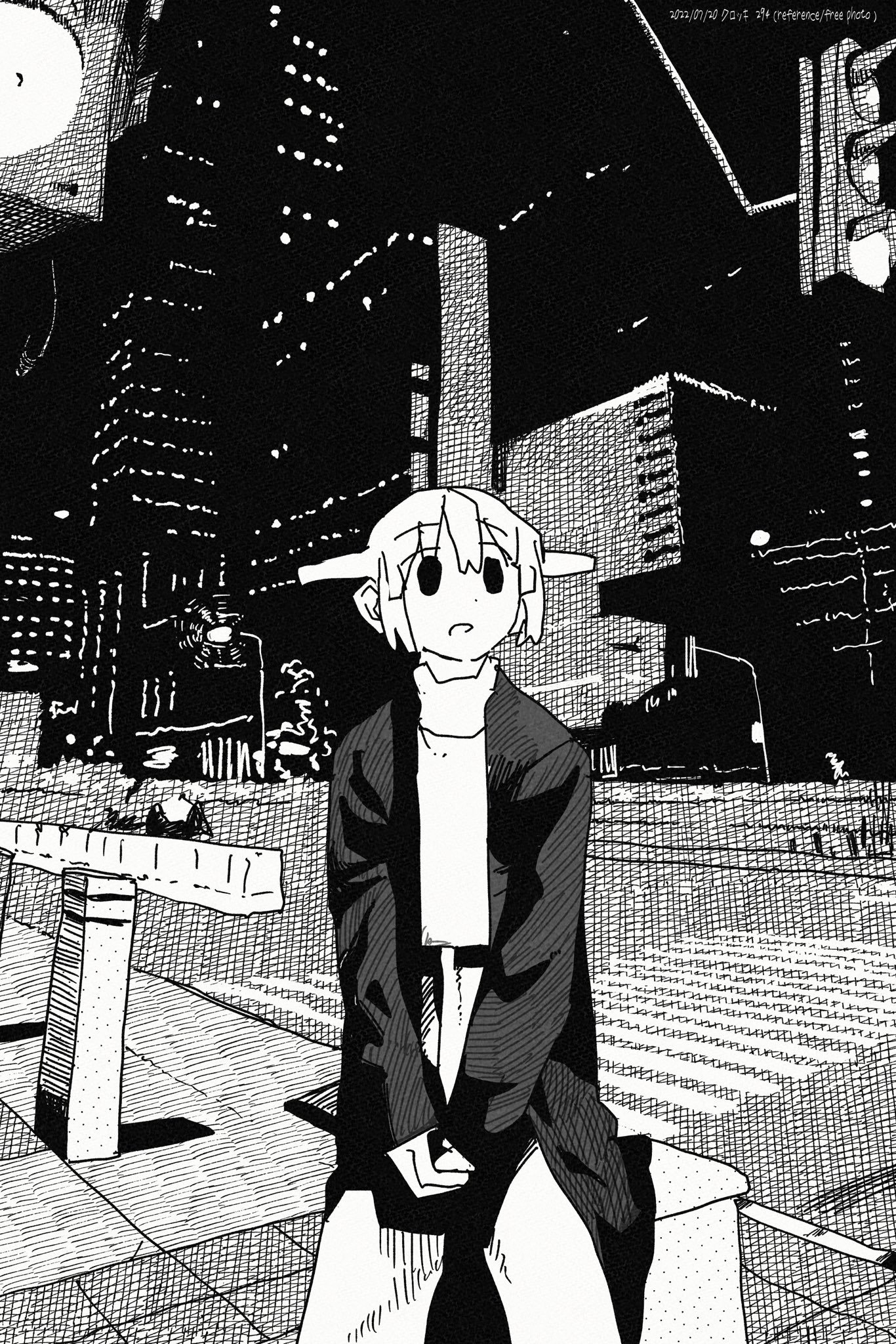女性主义的文明性与to be mean的权利
刻薄女孩的女性主义: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何心理操纵、搞小圈子和迈向精英Mean Girl Feminism: How White Feminists Gaslight, Gatekeep, and Girlboss
Kim Hong Nguy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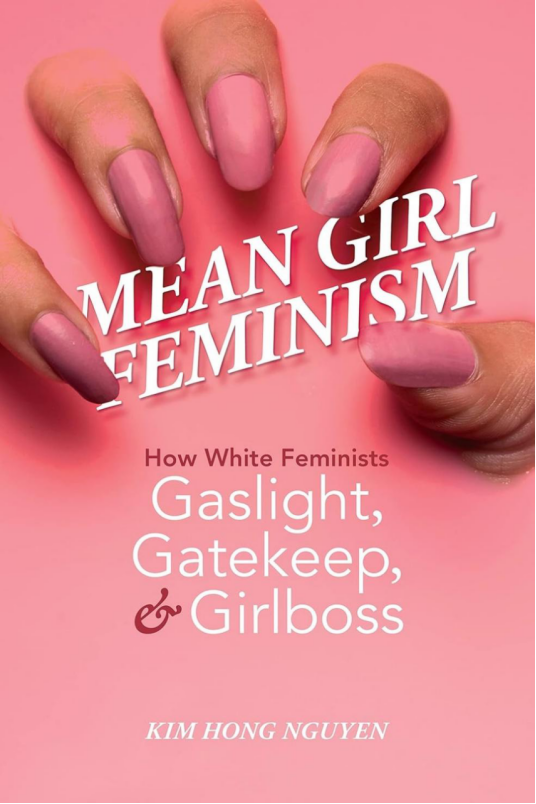
引言 · 女性主义的文明性与to be mean的权利
镜头拉远,红色幕布在舞台上徐徐开启。乡村音乐人泰勒·斯威夫特登场,以她那白人女性的声线作出指控:“You! with your words like knives / And swords and weapons that you use against me / You have knocked me off my feet again / Got me feeling like a-nothing.” 开场景设在美国南方的乡野意象中,她的乐队弹拨班卓琴与手鼓。歌曲“Mean”(2011)的音乐录影呈现:一位白人酷儿男孩被橄榄球队霸凌,一名白人女服务生为大学学费打工储蓄,一位白人短发女孩因胸前的蓝丝带(象征反霸权的女性身份)而被排除在午餐谈话之外,以及霉霉本人被绑在铁轨上,面前是她醉醺醺的白人男友。副歌昂扬高奏:“Someday I’ll be living in a big old city / And all you’re ever gonna be is mean.” 此时,霉霉打断乐曲节奏,用“主人的工具”来对付meanness:“All you are is mean / And a liar / And pathetic / And alone in life / And mean, and mean, and mean, and mean.” 场景随即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成功想象:乐队在纽约百老汇演出,那位被霸凌的男孩如今成为时装设计师,服务生成为企业高管,而我霉解开绳索——这些绳索从一开始就并未系紧。1 “Mean”最终以佩戴蓝丝带的女孩在台下为霉霉鼓掌谢幕。与她的其他歌曲一样,“Mean”展示了霉霉为人熟知且饱受质疑的名人形象:她以创作作词作为一种创业式的“出气口”,将自己营销为一位被前任男友(最近又以一种反讽的“antihero”姿态承认“问题在我”)伤害的白人女性。2 然而,爱他的人却是她;爱并驯化白人男性气质的,正是白人殖民女性身份。通过将霸凌与言语攻击命名为“mean”,霉霉暗示,meanness支配着性别与性取向在异性恋规范化、种族化与阶级化主体性中的纳入与排除。

这首歌曲,置于霉霉的名人身份之中,让我们看到“mean girl 女性主义”之生产性权力的缩影:即白人女性如何栖居于一种德性化的道德领域,使女性主义得以作为embourgeoisement(布尔乔亚化)运作,一种新自由主义式的种族与性别上升通道。3 mean girl 女性主义在白人愤怒之际,为白人异性恋规范的女性身份提供了高贵的复兴——允许白人女性将“bitchiness”作为女性主义的表演性来“再占有”,从而与种族主义“微侵害”的话语拉开距离。歌曲中的白人殖民特权,推动了从小镇到大都市、从最低工资到固定薪酬、从关系性约束到个体与自由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迁移。霉霉通过点名(他)的个体“mean”,使殖民主权结构带上女性主义的魅力与正面情感,如同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并不mean、且可以对边缘群体敞开怀抱一般。曾经是meanness的受体,霉霉通过歌曲与商业化的白人男性凝视获得赋权,展示出在应对性别歧视时将自我呈现为无辜,正是她自身施展meanness的可能条件。
以霉霉为例,有助于说明将mean girl 女性主义命名并召唤为现实之表演性矛盾,包括我在此谈论她时也难以避免这点。我意识到,指控mean girl的meanness本身也是某种meanness。然而,正是关于霉霉的这一公开的“秘密”,使她成为mean girl 女性主义的典型。她“落难少女”的人设一方面是熟悉的母题,另一方面则是掩饰她自身白人meanness的权谋。2009年坎耶·韦斯特在她的获奖致辞上台打断的事件众所周知;多年后,侃爷在其歌曲“Famous”(2016)中提及霉霉,霉霉公开否认她曾同意这句歌词,直到侃爷当时的妻子金·卡戴珊公布了一段电话录音,显示事实并非如此。对许多人而言,此事昭示了“白人的两面性”。对被种族化的人群来说,白人两面性再熟悉不过。置身白人至上体系的“落难少女”,一直以来也就是mean girl;这是一种二元性,曾被“白性”否认,而今却被女性主义所礼赞。(译注:很想吐槽一下这段,但还是算了)
霉霉的音乐与名望,正好体现了性别研究与白人自由派女性主义所制造、并声称要解决的那类问题。本书考察meanness与其他负面情绪如何将白人女性的表演与传播实践常态化为女性主义与反父权的举动。我的目的在于探究女性主义如何指向“性别”,仿佛“性别”本身就等同于抵抗。通过剖析那些借由异性恋规范的性别表演性的mean girl 与女性的女性主义话语,我主张:女性主义将白人mean girl定位为抱怨与成熟文明的理想化形象。女性主义设想出一系列情境,要求以“性别”这一范畴来理解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并提出应以meanness来对抗与反制之。关键在于,女性主义一方面将mean girl界定为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敌人,同时又宣称正是mean girl的表演性为父权提供了“所需的修复”。女性主义认为,mean girl之所以是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问题,在于她们违反了“女性”规范与训令。然而,充满反讽与俏皮的是,女性主义又将mean civility视为一种挪移并抵抗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能动性。在mean girl 女性主义中,mean girl通过披戴“非白人种族化”和“黑性”的特征来戏剧化与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对峙,从而代表一种新的主权——更“良善”的主人与更平等的权力利益。
正如Koa Beck所言,“对于white feminism(以及白人和可被视为白人的女性)而言,抗议是一种安全的事业。”4 mean girl 女性主义鼓励将白人女性的“女性性”表演为一种攻击性。5 虽然我将meanness限定在mean girl 女性主义的脉络中加以追踪,但我们身处的时代,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其他纪律性权力将人际话语暴力自然化的时代。《多伦多星报》的Vinay Menon发问,我们是否生活在一种“culture of meanness”当中,在其中粗鄙与争斗可能具有传染性。6 学者Melissa Gregg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工作条件鼓励劳动者去人格化并减少人际互动,偏好“user friendly”的沟通方式——技术上友好,却并非真诚友善。7 电子邮件与其他文本型消息取代了人际接触与关系性,几乎不留空间用于联盟建构与关于工作条件的对话,却拓展了meanness出现的可能性。雅虎新闻的Soraya Roberts推测,meanness是那些名列《福布斯》收入榜首的媒体名人最共同的特质。8 这种meanness文化与话语暴力支撑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与对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结构性不平等的自由放任。媒介化暴力的研究者指出,相较以外星人或奇幻生物为对象的游戏,瞄准“恐怖分子或罪犯”的暴力电子游戏更受欢迎。9 这种对人类与刻板形象的暴力再现,复制了标志现代性的殖民暴力“去中心化”。若米歇尔·福柯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君主制与专制衰落之际萌发的种族主义,那么Ann Laura Stoler与其他学者则指出,伴随君主制衰微与自由主义兴起的19世纪,正是殖民种族主义的现代形态。Stoler将以“非暴力”之名替代赤裸专制为“embourgeoisement”,用以描述白人移民女性与白人核心家庭规训如何被召唤进殖民治理之中。10 Stoler对殖民暴力去中心化的研究显示,帝国对“性别”的关切如何与殖民对种族等级、优生学、礼仪规范与社会期待的投资彼此渗透、相互赋权。与Gabrielle Moss及其他女性主义学者指出“女孩被视为meanness文化的肇因,并被刻板化为比男孩更mean、更具攻击性”不同,Stoler认为,白人女孩与女性表演的meanness,反倒滋养了殖民社会“非暴力”的观感。11
女性可以做什么、说什么、穿什么;女性可以去哪里、在何处工作或娱乐:这些一直是白人自由派女性主义试图扭转、扩展并使之无边界化的议题,旨在创造一种“反抗中的落难少女”,以回应将白人女性刻板化为对“顽劣孩童与忘恩丈夫”温柔体贴的“贤妻良母”角色。也许,“表演性”是对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之号召的回应——“为女性书写并把女性带入书写”,以便“让女性回到她们的身体——那个被没收、被转化为陈列的诡异异物的身体”。12 然而,被陈列的不仅是性别化的身体,更是白人的身体,因为白人女性被置于实现并流通女性主义承诺的位置上。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2015年就任时,组建了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届性别比例均衡的内阁。以“性别”框定的问题,如“工作—生活平衡”,似乎通过纳入准备好表达自身需求的白人企业家式女性而得以解决(例如雪莉·桑德伯格在《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中所倡导),尽管有色女性一直都在lean in。13 2014年,抗议被转化为时尚,多数为白人模特在香奈儿的T台上举牌:“Feminism Not Masochism”“Ladies First”“History Is Her Story”。在大学课堂中,构成“多样性”总体感与平权行动主要受益者的往往是白人女性。14 不幸的是,这种仅以性别为中心的女性主义——使白人女性在教育、职场、政治与媒体中得以纳入——并未被理解为白人威望的延续与白人女性embourgeoisement的产物,而被视作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对父权权力的“正向”效应。15 正如Beck所言:
这种路径让把你对社会正义的全部期待寄托于一位不推动体面医疗福利的年轻女性CEO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庆贺。它使得她只关注自己的工作绩效与产品指标、并剥削公司里其他所有人低薪而超负荷的劳动也变得足够了。它让她依赖一支稳定的移民保姆队伍以便她能做这些工作也变得理所当然。因为改变会以“一次一个女性”的方式发生。我们通过支持“她的独一性”来支持女性主义。16
尽管酷儿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与何塞·穆尼奥斯的里程碑式著作关键在于挑战性别本质主义,但“在男性世界里作为女性的挣扎并要求被纳入公共机构”(扩展女性能动性的努力),却在无意间催生了关于传统性别表演性与其他“女性性”传播方式的理论与批评。许多关于女性主义表演性的论述忽略了他们在性别表演性方面作为酷儿与跨性别介入的关键洞见,转而重新稳固一种为异性恋规范、“白性”与“以显见的、表皮的差异偶像学融入当代技术的商品陈列……以致破坏那些以排斥、沉默或不可见为枢纽的政治分析”的女性主义。17
女性主义无法解决由其存在本身所引发的主要问题:异性恋主义以及性别二元与差异化之问题。将身份生产压缩为“性别二元”,女性主义让“种族”被抹除并变得无关紧要。Ruby Hamad指出,白人女性身份通过拒绝拆解使所有人失权(包括白人女性自身)的“性别二元”,从而帮助维持白人支配。18 女性主义的价值导向催生了以女性为中心、由女性创作的剧作、性别研究课程、性别差异研究,以及反歧视的政治组织与行动。但在北美,这种女性主义的“以女性为中心”,结合“性别二分”的逻辑,已经走向了歧途。确实,另一种“性别不平等”的基调需要我们的注意。承认女性作为有能力的领导与创意愿景者的潜能,如今可以被廉价地购买:印着“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Boss”的T恤与马克杯大行其道。同样流行的是“boss bitch”的新词,以及不断增长的女性自助类书籍市场,教导如何在职业与其他领域中部署策略、拥抱她们内在的俏皮的mean girl。《Mean Girls》(2004)等票房大片与《Gossip Girl》(2007–12)等充满争议但广受欢迎的剧集,将白人mean girls争夺社会等级顶端戏剧化。2008年萨拉·佩林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时,她被称为mean girl,同时她也指责媒体“mean spirited”,促使自由派作者Melissa McEwan开设博文系列“Sarah Palin Sexism Watch”。19 同样,性别研究将mean girl既视为后女性主义的征兆,也视为限制女性主义发展的形象。通过以女性为中心,女性主义允许白人女性将自己的异性恋与顺性别性理解为一种“反叛”,并为那些把门并排斥酷儿与跨性别议题的mean women提供保护。萨拉·艾哈迈德也识别出我称之为mean girl 女性主义的“走偏”:她不仅强烈呼吁女性主义者遵循奥德丽·洛德的号召(“不要成为主人的工具!”),还讨论了女性主义如何动用“‘任性之指控’来制造一种印象,即自己是与社会舆论之潮抗争的孤独激进女性主义声音。他们利用这种必须抗争的印象,来阐述一个反对跨性别者的立场——而跨性别者必须为存在而抗争——这种立场阐述得如此激烈,以至只能被称为仇恨言论。”20
此外,女性主义忽视了使其“必要”这一条件存在的根本:底层者的生产,以及那些无法以可理解方式表达其内在知识之人的处境。正如Alexander Weheliye所言:“问题并非语言本身的匮乏,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底层者不能发声,而是关于受制者所能使用的言语类型,以及见证其困境之人如何看待与倾听这些言语。”21 实际上,将“善于言说的舌头”礼赞为“女性主义反叛的器官”,本身就是能力主义的。22 Jay Dolmage讨论了面对学术精英主义的过程如何要求边缘学生自我陈述其需求、界定其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23 艾哈迈德建议我们“学习如何倾听不可能之物。这样的不可能倾听,唯有在我们回应一种并非自身之痛时才有可能。”24
沿着Jessie Daniels关于white feminism并非单一体、而是存在多种变体的论述,我希望检视某一特定类型的白人女性主义如何走向歧途。25 以mean girl话语为研究焦点,我发问:meanness为女性主义生成了何种功能?meanness以何种方式赋予女性主义一种“反抗”的声调?为了成为一个“女性主义主体”,有哪些东西被预先封闭与排除?我提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想思考在mean girl 女性主义时代,抵抗更难以定位,而女性主义解放更难以想象。以Stoler关于embourgeoisement作为一种去中心化暴力的概念为起点,我追问:女性主义如何成为白人殖民工程的一部分,去创造对资本主义忠诚的劳动者、在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中“有爱”的主体,以及其毒性受到“性别二元”保护的白人女性?我想探究,被白人女性主义推动而获得承认的“性别不平等”——对其来源的假定、对其补救之道——如何延续并生产种族伤害。若如Hamad所言,“落难少女”通过将有色人群转化为暴力的靶标而攫取他们的“无辜”,那么“mean girl”这一形象则通过窃取被种族化的抗议方式而攫取“反抗”的修辞。26 如同霉霉在她的“Mean”音乐录影中那样,mean girl 女性主义通过将被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束缚的“落难少女”转化为“反抗中的落难少女”,来表演被种族化的对性别压迫的抵抗战术。
将“性别表演性”扩展到包含“the right to be mean”,是白人女性主义不满情绪的新边疆;然而在这一边疆之中,潜藏着女性主义“非表演性”的主要断层。沿袭艾哈迈德关于“非表演性”的模式,我认为白人女性的表演性“恰恰通过未能带来其所命名的效果而发挥作用”。27 我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对“表演性”的转向,视为与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一次异性恋式的调情。28 女性主义中的性别表演性,是一种“非表演性”,旨在召唤一个将个体表现、机智与聪明凌驾于共同体韧性与团结之上的世界。
通过分析1970年代之后与民权运动之后那些将mean girls/女性塑造为父权之“对手”与“解药”的话语,我展示:女性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性别化自我”的场域——而“性别化自我”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无法脱离其他身份轴线或其历史语境而独立发生。相反,女性主义是一个通过将meanness视为反父权的表演性,从而为“白人主体性”生产“性别这一体裁”的场域。我主张,meanness将女性主义规训进“白人情感网络”。在它关注“表演性”而非反殖民自由与去殖民解放的过程中,mean girl 女性主义将“自恋”动员为其身份政治的构成部分。作为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敌人”与“修复者”,mean girl这一形象唤起一种将女性主义进步叙述为“反叛”的故事;与此同时,她那“主角能量”又以girlboss之姿态通过“煤气灯操纵”(gaslight)与“把门”(gatekeep),使白人得以免于关注他们在维系当前压迫体系中实施的暴力。
在本书的行文中,我将说明女性主义如何发展出一种以“性别”为本体的压迫观,通过贬抑“被种族化”与拒斥关于种族化压迫的知识,来把白人女性定位为比肩白人男性的最佳主权者或“平等的主人”。Daniels直言不讳:“我所遇见的一些最坚定地认为‘谈论种族会分裂人群’的倡导者,恰恰是白人女性主义者。”29 不认为自己是问题的白人女性主义者,最难被说服她们确实是问题之一。我延续Stoler、安吉拉·戴维斯、Sabine Broeck、Alexander Weheliye等众多学者的工作,去复杂化性别研究,复杂化白人女性在西方制度建构中的角色,归根到底也复杂化“女性主义”这一词。奴役主义(以及白人女性挪用黑奴的“奴役”来标记自身受压迫)、对黑人女性思想的不署名挪用、白人的“全球母职”与通过“权力伴侣关系”展现的白人新自由主义异性恋关系性,都是推动白人女性上升并流通女性主义承诺的修辞策略。mean girl 女性主义鼓励白人女性拒绝看见自身问题性,拒绝承认她们即是问题,或者即便承认,如同泰勒·斯威夫特本人,也拒绝因此作出任何改变。
我选择了1970年代后与民权运动之后那些转向“表演性”与“the right to be mean”的论述,恰是因为其“女性主义潜能”。女性主义对“表演性”的转向,标志着对“女性主义是什么、谁可以成为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实践何以呈现、以及其目的何在”的焦虑。作为一种“非表演性”,meanness一方面标示了对女性主义的真诚承诺,另一方面又遮蔽了对“仅致力于性别平等”的严格奉献所造成的伤害。我要问题化的是:mean girl 女性主义并未建立或运作一种以“破除压迫”为旨归的女性主义。mean girl 女性主义通过把她的“闺蜜团”、她的“能言善辩”、她的“权力伴侣”、以及她对被她视为“值得者”的“母职化”悉数调动为她的成功与上升,从而进行“煤气灯操纵、把关与girlboss化”。女性主义与性别研究中的“表演性转向”本身就是一种表演政治,也是一种“非表演性”,因为它同样拒绝清晰阐明一种面向集体自由与解放的文化与社会政治愿景。
白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文明性
当处于男性主导空间中的“受压白人女性”的脆弱性成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时,这种脆弱性的影响需要被理解与追踪——一些白人学者确实已对“有毒的白人女性性”表达了关切(例如Laura Kipnis、Wendy Brown、Louise Michele Newman、Kyla Schuller与Jack Halberstam等)。30 正如Mamta Motwani Accapadi对这种微妙的“无助”所言:“白人女性既可以是无助的——而这种无助并不会被视为全部白人的反映——也可以是有权势的,因为她们同任何白人一样占据权力位置。”31 Stoler在其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亚欧洲殖民地的个案研究中所写,对于21世纪的北美同样适用:“欧洲女性不仅是种族主义信念的真正承载者,还是将种族主义付诸实践的强硬执行者;她们鼓励白人内部的阶级区分,同时滋生新的种族对立——这些对立此前被性接触所消弭。”32 作为“女性”的原型,白人女性通过要求体制支持、法律改革、预防性或惩罚性措施而确保了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地位——而这些措施对有色人群相当有害。然而,她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常被忽视:例如Stephanie Jones-Rogers指出,历史学家常忽略白人女性在奴隶制中的角色,基于“性别歧视在法律、经济与社会上阻止女性持有奴隶”的假设。Jones-Rogers以实证材料记录:对白人至上将黑人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的承诺,白人女性与白人男性同样深度捆绑,甚至更甚。33 Wendy Anderson同样指出,白人女性在延续白人至上结构中的重要角色:“白人女性可以被塑造为受害者、欲望客体与容器,从而为她们支持白人至上主义辩护。”34 因此,到20世纪伊始,“白人女性被置于一种新‘道德秩序’的中心,被作为白人繁衍的基石。”35 在对美国南方“白人女性作为母亲与妻子如何团结起来,以‘保护’其家庭与民族国家免于被他者(被种族化者)侵入”的研究中,Elizabeth Gillespie McRae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白人女性塑造并维系了白人至上政治。”36 Ruby Hamad显示,“白人女性身份、女性主义与白人至上”的关系有利于白人女性上升:“白人女性能够在‘性别’与‘种族’之间摇摆,在‘被压迫者’与‘压迫者’之间切换。”37 Schuller则论证:“白人女性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它未触及什么、漏掉了谁……而在于它做了什么、压制了谁。”38 这些学者提示:文明性是白人女性进行种族化工作、并对阶级区分、社会互动与公民参与进行“把门”的中枢。
在其关于“消灭女性不胜任”之女性主义议程的论述中,Kipnis解释:“‘女性性’是将女性劣势创造性地转化为优势的方法,基本上就是做那些有助于与男性建立战略联盟的事。”39 这一议程与“黑人女性主义”内在对立,正如Koa Beck所述:“像男人那样行事或获得男人拥有的东西,或实现与男人的等同,不仅目光短浅,而且被认为天生带有压迫性,因此不符合黑人女性主义。毕竟,使得男人拥有之物与历史性行事方式成为可能的机制——父权——本就依赖对他者的剥削。”40 支撑“女性主义主流化”的,是一个被漂白的童话,宣称女性主义的道德旨趣在于建立“男女平等”。按照这一殖民叙事,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造成了两大不公:通过剥夺投票权实现的政治性剥夺,以及通过薪酬不平等与角色差异实现的职场歧视。美国的白人女权参政者(如苏珊·安东尼)在性别平等这一“正义目标”的鼓舞下,自以为其种族主义理所当然。Newman记录,女性参政动员植根于白人对黑人、原住民与亚裔人口“上升”的焦虑。41 Beck有力地论证,第一波的“仅坚持‘性别歧视’”将成为白人女性主义与所有其他人(酷儿、非白人、工人阶级女性主义)的“根本与持久分歧”。这既是白人女性主义在后续各波动员中的定义性特征,也是它们继续为之奋斗并据以想象“性别平等”的基底。42 与其像安吉拉·戴维斯所倡导那样将家务劳动“工业化”,女性主义敦促白人女性进入职场,并雇用移民女性与有色女性来打理家务,同时挽救她们的婚姻与异性恋式“美满同居”形象。43 其后果是全球性的:例如在波斯湾战争(1990–91)期间,全国妇女组织与“计划生育协会”将反战批评降至最低,把焦点放在“那里的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并将有色女性呈现为女性主义的“沉默受益者”。44 女性主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殖民轨迹的一部分,其中白人女性充当性、别、种族与阶级之“把关者”,以确保自身地位与信誉。
在题为“白人女性的眼泪”的章节中,罗宾·迪安杰洛指出:“在被迫之下,白人男性可以承认白人女性的人性;白人女性是他们的姐妹、妻子与女儿。当然,通过这些关系,白人女性对资源的增加也会惠及白人男性。”45 这种对资源的“增加”将我们带回Stoler的embourgeoisement概念,她以此理论化白人女性在殖民地发展中的角色,以及(如Vron Ware所写)“‘性别’如何在组织‘种族’与‘文明’的观念中发挥关键作用,女性也参与了帝国的扩张与维系”。46 embourgeoisement是白人女性与白人男性一同追求欧洲声望与地位的殖民过程。47 虽然其原初含义只是“工人阶级通过采纳中产阶级的价值、信念与消费风格而与之趋同”,但在Stoler处,embourgeoisement标示的是通过“白人女性脆弱性—白人威望—种族紧张”的凝聚,在东南亚欧洲殖民地内生长起来的阶层分化。怀揣对更好生活的追求并享受新获特权的定居女性抵达殖民地后,坚持要有私密空间、都会式设施与种族礼仪,以为“对原住民的性焦虑”设立门槛。embourgeoisement开启了一种看似“非暴力与进步”的“殖民文明”,以生产“种族边界”来塑造一个资产阶级定居主体性,并稳定殖民治理。48 这种以“进步改革”之名的embourgeoisement,改造了殖民压迫的各种实践,通过在原住民与定居者之间、以及其内部组织权力关系来进行。49 在当代都会中,embourgeoisement延续为文化偏见、城市绅士化与郊区围篱,这些暗示“体面”“整洁”的审美来自舒适居住于此的白人“道德资产阶级”(尤其是女性),以及被安置在他处的非白人与工人阶级。50
Cecily Jones确认,追求承认需要对“性别与种族的关系”采取细致的处理:“将白人殖民女性呈现为父权之受害者,有助于阐明‘白人男性对白人女性身份、身体与性之权力’,却几乎无助于理解‘性别如何被种族中介’,以及‘作为被建构之社会客体者如何在追求主体性的过程中挑战自身被界定地位’。”51 沿着Schuller关于白人女性主义运动“由一个幻想驱动——即白人女性的参与本身会改善文明”的论述,我发问:女性主义如何作为embourgeoisement的“进步改革”,以提升现代统治术的道德品格?52 也就是说:女性主义如何通过重组权力关系与对白人女性“教化角色”的感知,改变殖民压迫?旨在扩展“承认政治”,将mean girls与女性囊括在内的女性主义表演性与其他传播实践,又以何种方式促成embourgeoisement?尽管我无法完整描绘女性主义如何作为殖民统治术之技术而运作,但我将勾画出1970年代以来关于女性主义“表演性”的话语如何推动“文明性”与当代embourgeoisement之进程。
“文明性”作为一种社会调解者,通过表演性分散权力,从而引发“公平与平等”的感受。传统礼节与礼仪等旧式文明规范,在崇尚平等与个人意志的现代民主社会中作用渐弱,这使得权力关系更不易辨识。随着“开门”等历史性的“侍从之举”不再严格沿着阶级、性别与种族划线,骑士式举止或得体餐桌礼仪已不再是贴近或远离权力的有效指示。相反,现代文明性通过“辱骂、冷言冷语、策略性否认与负面情绪”来管理社会关系。愤怒是对歧视的健康回应,不快乐是对社会与制度排斥的正常反应,嫉妒是对不平等的感受。53 meanness传达并回应着“与权力的距离感”。称呼有色女性“mean”或以“bitch”相指,是把她们“放回原位”的努力,是提醒她们远离权力、将自己定位为权力持有者,并通过社会关系来分散权力。
因此,我质疑把“文明性”视为“冲突的替代物”的通俗理解:在殖民主权之下,所有社会关系都受“文明性”规训。故而,我不同意乔治·阿甘本所持的通俗用法:他将文明性界定为与“粗暴武力”对立之物,认为在“例外状态”(或扩张的国家权力,如殖民地)中,国家代理人成为法律“公平适用”的仲裁者,暴行是否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临时充当主权者的警察之文明性与伦理感”。他写道:“在一种有效但不具指称性的法律下生活,就像在例外状态中生活,在那里,最无辜的举止或最细小的疏忽都可能带来最极端的后果。”54 与将“文明性”视为在发生冲突、政治撕裂或极权统治时“摇摇欲坠”的阿甘本相反,Benet Davetian回溯更早的欧洲史,展示“文明性(连同礼貌实践)在中世纪早期被构想为‘一种用以合法化新酋长权利的恭顺与颂扬过程’”。根据中世纪“礼貌学”的史料,权力在此时期发生了转移:远离男性赤裸暴力,朝向一种“君主的贵族化区分”。55 骑士精神不仅通过将其引导至“有利于主权者愿望的方向”而驯服男性暴力,还调解了主权者宫廷内部的性别关系。从礼节到礼仪,从沙龙与咖啡馆中的谈话艺术到礼貌,文明性的各种规范与门类,既是维护身份地位的工具,也是建立贵族与非贵族阶层之间“等级”的手段。因而,“文明性”与调节“得体行为”的机制之所以发展,不仅因为主权者需要将暴力控制并导流到有利的出口,还因为主权者代表的是“非军事的个体、群体与制度”。Davetian总结说:“我们更应将文明性视为一种双边过程,一手是克制,另一手是攻击与策略性行为。”56 换言之,“文明性”并非如阿甘本所言,是一种在冲突文化、分裂社会或法西斯与极权政府中缺席的“脆弱过程”。恰恰相反,文明性正是所有权力体制通过暴力进行统治的中枢。
Tavia Nyong’o与Kyla Wazana Tompkins指出,“文明性是行政性暴力的情感外形”。57 文明性构成了人际关系的空间:令主体各安其位,正当化对一些人的排斥而非另一些人,并抑制特定行为。文明性的关键吸引力在于,它一方面“肯定主权权力的奇观性展示”,另一方面“将判断延宕至法律之力量”。也就是说,当meanness正在执行“文明性”对“身份地位与恰当表演性”的划分工作时,要求更多“文明性”的呼声就会出现:“让我们文明地分歧吧。”与此同时,当meanness指向(并威胁)权力关系的脆弱性时,也会出现“需要更多文明性”的呼声:“她不文明,越界了。”简言之,要求更多“文明性”往往不是对“友善或非暴力”的呼吁,而是对“向既定可理解性与权力常态靠拢之沟通”的呼吁。
诸如说“请”、在谈话中回避政治等行为规范,将“接近与远离主权”的关系常态化,同时放大那些“值得获得权力宽宥的身份与具身性”。Schuller阐释了我所谓“女性主义文明性”的内涵:
在white feminism之下,“性别正义”的目标被缩减为“捍卫女性的品质与身份”。当下的议程变成“赋权个体女性拥有自己的声音、拒绝被mansplain、拥抱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这些实践本身并无不可,但它们既未传达“性别歧视的摧残性”,也未提供可行的拆除之策。事实上,将“女性(Woman)”这一身份物化为女性主义政治的基底,反而使得将“性别歧视”识别为一种“剥削与攫取结构”变得更加困难。58
白人女性主义不去记忆“痛苦的来源与历史”,而是通过将伤口转化为身份,来物化“女性”。艾哈迈德沿着温迪·布朗的思路,提醒我们:过度投资于“伤口”,使“复仇”成为反应,而行动因此变得不可能。59 女性主义的文明性通过鼓励白人女性以“meanness”来协商关于政权决断的情感环境,从而维持社会关系,而非通过行动。若“礼仪与谈话艺术”显示的是特权与文化训练,那么meanness展示的则是“主权恩典之可能与限度”。当白人女性施演meanness时,她们提醒他人其与主权权力的关系:她们能够动用暴力,理应令人畏惧。Daniels言道:“我这只白人淑女的手指轻轻一指、向经理提出会面请求、或拨打一次911,我的身体就成为一种攻击性武器。”60 作为文明性的一个样态,女性主义的meanness在主权权力的臣属身上烙下这份“随时可能转为物理暴力”的潜能,并鼓励对规范的驯顺仪态。若“礼节、礼貌与行为规范”是权力机器顺畅运作的润滑油,那么meanness就是使政权不得不重新校准其力度、声调与形象,以支持白人女性embourgeoisement的那股“惯性”。若如劳伦·柏兰所言,“情感性依恋具有一种乐观的质地,使主体反复回到它们那里,即使在失望之下仍死死抓紧并不断重塑”,那么meanness恰恰帮助主体协商这些依恋的失败。61 文明性与其现代女性主义的meanness形态——“Bitch的表演性”、mean girl 女性主义、“权力伴侣关系”、全球母职——是结构化“乐观”的抵抗模态,而“性别平等”是那条不断后退的地平线,让主体始终抓紧不放。
女性主义已成为“演出”——权力兑现“平等”的舞台。女性主义的文明性,在霉霉的“Mean”与她的其他作品中得到了最佳概括:meanness成为性别不平等的一个宣泄口,却遮蔽了女性主义如何推动阶层流动与白人定居者特权。在mean girl 女性主义这一本身就“表演性矛盾”的体制中(既mean又指控meanness),霉霉成为“理想的抱怨者”,她既能因性别歧视而显得脆弱与无辜,又能因女性主义而显得mean与反抗。同样,作为一名教授,我发现性别研究及其课程是白人女性的理想场域,因为女性主义允许她们既肯认自己的“白人脆弱”,又将“女性”作物化。女性主义以一种“非暴力且进步”的姿态,似乎正在通过“表演性转向”来应对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而这只会让女性更加“向前一步”,更加努力去“认同”那些正确的女性主义能指。女性主义的meanness将注意力从“殖民暴力与主权临近性”挪移至“性别与女性主义的类别本身”。
女性主义文明性的“白性”
mean girl 女性主义将白人女性与白人男性之间的关系规训为对立且不平等,而非同频与合作。作为当代的一种“文明性”形态,女性主义的meanness组织了当代权力关系与“可理解性格栅”之间的交叉点,也组织了身份—地位维持—白人至上的交汇。同时,职场中的同事实施微侵害、朋友暗讽、约会场域中的“幽灵式消失”之外,还存在另一类形象,它们通过“正向强化”与“文明性”来施作:打破“不可触碰”规矩、与臣民握手的王室成员;与来访白宫的儿童击掌、拥抱婴儿的总统;向电视观众开放家居参观的名人。当“负面的文明性”与“法律的强化”被下放并分散给其他人(从警察与边境警卫,到政界的喷子与网络上的网络霸凌者)时,人们持续或再度欣赏那些“过度分享、直接与公众互动的”国家元首,并对那些有时间、精力与一般性特权、能耐心与粉丝交谈的名人心生赞叹,遂成常态。62

对纪律性权力之“扩散”同样关键的,是女性主义对“白人女性公平”的承诺,它启动了embourgeoisement(中产阶级化)。white feminism遮蔽了embourgeoisement如何再生产“有毒白人女性性”:一方面将白人女性置于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中的脆弱位置,另一方面又赋权白人女性施展meanness。女性主义的meanness助推了种族化与“种族拼组”的硬化;据Alexander Weheliye之言,这种拼组将“人性”规训为“完全的人类、非完全的人类与非人”。63 事实上,“有毒白人女性性”长期拥有却大体未被充分审视的修辞权力,并在历史上对有色人群造成暴力后果。关于“暴力的非白侵入者与强奸犯”的刻板印象,数十年来广见于媒介,从《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到《犯罪现场调查:拉斯维加斯》(2000–2015)。64 这种恒久的虚构,塑造了一个默认“残忍谋杀埃米特·蒂尔”(1955年因被指“对白人女性吹口哨”的黑人男孩)与“科尔滕·布希”(2016年被指“擅闯白人地产”的原住民男子)之早夭死亡的文化。对白人女性“安全”的维护,正是支撑针对黑人、原住民与其他有色人群之暴力的惩罚性逻辑的基座。用罗宾·迪安杰洛简练的话说:“我们(白人)的眼泪会触发这段历史的恐怖,尤其对非裔美国人而言。”65 除了在2016与2020年大选中大量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之外,白人女性还曾因有色人群做着“稀松平常之事”(例如烧烤)而报警;并且在性侵知觉上制造偏差,捏造对有色男性的强奸指控。66 近来,这种“有毒白人女性性”在Black Twitter被以“Karen”这一模因加以命名,用以指称白人女性如何将自己的脆弱当作伤害有色人群的武器。她的“发飙与崩溃”会让人蜷缩、畏缩,人人如履薄冰,生怕触碰她那“白人脆弱”的蛋壳。
我在援引“Karen”模因时保持谨慎:此模因容易把一些白人女性当作“边缘且极端”的替罪羊来谴责,从而转移对“有毒白人女性性之普遍性”的注意。然而,“Karen”模因指出:白人女性之所以能成为“最大声的抗议者、最激进的人与法律的执行者”,正在于她们知晓并愿意将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直言之,白人女性对于其他白人而言是落难少女;但对非白人而言则是mean girls。哭泣的“落难少女”会激发父权的保护、压制对其品格的批评;而“反抗中的女性主义落难少女”则是“以恐惧与厌恶相威胁的mean girl”。“Karen”模因、泰勒·斯威夫特、《Gossip Girl》中的角色,以及更多白人女性、她们的再现与女性主义方案,都在通过meanness的表演性参与“gatekeeping、gaslighting与girlbossing”。
在“将男性之权利与特权扩展给予女性”的旨趣之下,女性主义并未质疑那一理想化“正向主体”的范型:白人、异性恋、中产阶级、以启蒙理性为标识的男性。受Sylvia Wynter工作启发的学者指出,奠立并驱动女性主义的“性别”概念具反黑人性。既然“Man之体裁”(genre of Man)已被作为一种“有性别化的思维与存在方式”(如以mankind对照humankind)而遭到根本性挑战,那么Wynter主张,“女性主义之体裁”亦应作为一种“被种族化的思维与存在方式”而受到挑战。67 女性主义不过是对一个本已问题丛生之二元的翻转:即若“Man之体裁”被确认为“理性、启蒙、普遍”,那么“Woman之体裁”就被道德化为对“批判Man”的一种“受挫(亦令人受挫)”的状态。正如Wynter忧心“Man将自身过度再现,仿佛它就是‘人类’本身,并据此确保‘人类物种(我们自身)之福祉与因此之完全认知/行为自主’”,我也忧心“Woman将自身过度再现,仿佛她就是‘解放’本身、超然于主权”。68 在过度再现自身的过程中,“Woman”成为“解放”的主导能指;如Rafia Zakaria所述,她成为“解放必须流经的导管”。69 我们确应担忧,“Woman”既被用来标识“脆弱位置”,同时又被用来标示“殖民主义的人性与仁慈”的承诺。

与持续拒绝援引并富有成效地对话“黑人与被种族化理论介入”的倾向并行,据Sabine Broeck之言,西方的性别研究是由enslavism(奴役主义)所驱动的;其中,“黑人的被奴役主体”为“女性若要实现完全人类地位不应成为何者”提供了“隐喻的地平线”。70 当女性主义理论与虚构通过“想象白人女性被奴役以创造女性主义”时,它们便参与了enslavism。西方性别研究调动“囚禁的条件、意识与诸方面”——以及“黑人被奴役主体被赋予之各种意义方式”——作为自身的“负向参照与类比对点”。通过论证“白人女性并非奴隶”,女性主义便可将“女性之范畴”定位为“可与启蒙理性相容且胜任”——这一理性曾为“白人男性地产所有者”所独占。Broeck解释“enslavism如何对‘性别’的概念化不可或缺”:“一种进步且解放性的关于‘女性被性别化’的文本概念——该概念试图将‘女性’书写进启蒙、作为‘主体’,亦即为‘女性的抱怨与诉求’创造可理解性——正是通过‘书写女性非奴隶’而出现。”71 因而,“性别”这一概念之发展,服务于白人女性之embourgeoisement:主张权利的扩展;将家务劳动转移给被种族化女性;并确保白人女性的才智与精力被最大化运用,同时脱离与“被奴役主体”相联的一切。Broeck关于“性别研究如何将奴隶制隐喻化”的洞见,回应了安吉拉·戴维斯的观察:历史上,“拥有‘无法满足的家庭生活’的白人女性”如何动员对“妇女权利”的支持——“正是那些‘家境优渥的女性’在阐明婚姻之压迫性时,最直接地援引‘奴隶制’之类比……早期女性主义者很可能将婚姻描述为与黑人所受之‘奴隶制’同类,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的‘震撼效应’——她们担心否则她们的抗议之严肃性将被忽略。”72 Karen Sánchez-Eppler同意,在19世纪早期安吉丽娜·格林克、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苏珊·安东尼等人的文辞演说中,“女性与奴隶、婚姻与奴隶制”的修辞配对“倾向于不对称与剥削”,因为它“抹除了黑人与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并通过强调“性受害”,将“白人女性之性焦虑投射到‘被性化的黑女性奴隶之身体’上”。73 将奴隶制作为性别压迫的隐喻,说明“对黑人的压迫”不仅被否认,反倒成为“再生产并正当化白人女性主义embourgeoisement”的核心。在此意义上,女性主义话语重申了白人至上的宣称:黑人文化与经验“本属于它自身”。74

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上将黑人与被种族化女性排除在女性主义话语之外”的方式,使“性别概念”得以成为“看似非暴力且进步”的embourgeoisement工具。戴维斯记录了黑人女性被排斥于“参政组织”之外,不仅因为“白人女性可能因此退出”,还因为一些倡导者认为“女性参政权”将为“白人至上”带来巨大优势:扩大白人的政治主权,维持白人支配。75 类似修辞同样出现在白人女性主义对“避孕与生育权”的推动中:对于“特权者”被要求为“权利”的事物,被解释为“穷人”(包括女性、黑人与移民)的“义务”,成为对边缘群体人口的控制。76 通过将黑人女性排除出“女性及其相关范畴”(母职与持家),母职意识形态便与捍卫白人至上不可分离,“家庭主妇”的角色也转而成为“经济繁荣的象征”,而非“性别压迫的象征”。77 戴维斯揭示,女性主义的“主要目标——亦即成就”,乃是白人女性之embourgeoisement,她们进一步推进了“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Kimberlé Crenshaw将“单轴分析身份之问题”应用于“女性主义与反种族主义”,显示“将种族与性别当作相互排斥的经验与分析范畴”的倾向,如何抹除了黑人女性的经验。78 虽然Crenshaw对“反歧视法”的批评说明了需要“交叉性”的身份理解来防止这种抹除,但“交叉性女性主义”也已被白人女性主义者所挪用,用以装作承认自身的“情境性”与她们与其他边缘群体的“关系性”。Patricia Hill Collins对此早有预见:“替代性知识主张本身很少威胁既有知识。此类主张常被忽视、被否定,或被吸收并边缘化于现有范式中。更具威胁的是,替代性的认识论对‘强者用以正当化其知识主张’之基本过程发起的挑战。”79
这种对白人女性的embourgeoisement,使“种族资本主义”得以侵蚀“障碍的表象”,并将注意力从其他形式的压迫上转移。为了凸显白人女性在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中的脆弱性,女性主义策略性地将白人女性自身的(新)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之工具,铸造成“基于性别的痛苦来源”:她的bitchiness、她的“闺蜜小团体”、她与“坏男人”组成的“权力伴侣联盟”、她对“母职”的渴望、她与其他女孩/女性的竞争。与霉霉在其名人形象与“Mean”音乐录影中的呈现相似,mean girl 女性主义将白人女性的资产阶级抱负正当化为“性别化的路径”,并被赋予“白人道德德性”。本书概述了那些使白人女性把“异性恋规范的性别表演”视为女性主义斗争之“首要领域”的传播策略、能指与机制。
白人女性主义的主权与能动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理论通过发展并细化“能动性”的概念与示例,来驾驭“权力—表演性—主体”之间的关系。Saba Mahmood指出,在这一“后1970年代的女性主义框架”中——该框架分析参与与颠覆父权规范——“能动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一个“自律且抵抗的主体”的行动:她(他)违抗或重新部署霸权实践,以服务其“自身利益与议程”。80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学界对巴特勒“表演性”这一影响深远概念之解读,“能动性”几乎与“抵抗”同义,后者“向‘进步政治’强加了一种目的论”。“抵抗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寻求从权力中“获得自由”;其反面“驯顺”则等同于“取消能动性”。将“能动性”与“抵抗”同一化的后果之一,是“让我们难以看见并理解那些未必被‘颠覆—规范铭刻’叙事所囊括的‘存在与行动形式’”。81 Mahmood解释,“抵抗/臣服”的二元,使我们难以想象:抵抗话语如何一方面“质疑严格的女性行为规范”,另一方面又将“女性更深地固着进其他权力矩阵”。我进一步探究:这一“聚焦表演性”的后1970年代女性主义框架,如何以一个“自律—抵抗主体”(即“白人顺性别异性恋女性”)来想象“能动性”——或者用Mahmood的定义,即“特定从属关系所创造并使之可能的行动能力”——而该主体以女性主义来“修饰殖民目标”。82
女性主义的文明性,被“在白人异性恋男性凝视之下拥有the right to be mean与叛逆”的权利所界定。随着“表演性转向”,女性主义愈发着眼于“保护白人女性气质被个体化的表演方式”,却不对“白人女性性如何支撑其他形式的压迫”承担义务或给予关切,也不关心社会语境、流行刻板印象或自身行为的有害后果。女性主义的文明性,将身份作为“伤口”,使白人女性得以“以性别之名”为其生命中的问题与解法命名,而忽视“身份并不可还原为性别”。
本书围绕四个术语展开,这些术语通过将“文明性”规训进“白人情感网络”,来扩展“白人女性的表演性”:围绕“Bitch”标签的争议(第1章,以The Bitch Manifesto为代表);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的二分(第2章);“权力伴侣”的兴起(第3章);以及“保守女性作为女性主义者的身份”(第4章)。我之所以关注这些术语,也在于我也被鼓励使用它们来建构自己的“伦理区分与地位”,但在此我将它们问题化为“武器化”的工具。每个术语都展示了white feminism如何实施embourgeoisement与“定居者的无辜化转向”(settler moves to innocence)——这些策略“以问题化方式试图调和定居者的负罪与共谋,并拯救定居者之未来性”。83 这些“无辜化转向”既是“定居者式的”,也是“女性主义式的”,因为它们将“女性化的表演光谱”常态化为“与女性主义之未来相关”的事物,同时逃避白人殖民责任,并将“集体自由与解放”拒之门外。若“白性”作为一种“现象学”使“事物唾手可得”(依艾哈迈德),那么被白性所浸染的“女性主义文明性”,便使“meanness”触手可及,成为一种“可在不致遭遇社会性死亡的情形下表达”的常态化情感。84 作为一种“白人现象学”,女性主义文明性可以呈现为“对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抵抗”,而不必为这种抵抗“失去一切”。
“抵抗即能动性”是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话语中久经锤炼的主题;“Bitch”一词也曾被理论化为对“历史与当代女性形象再现”的女性主义违抗。“Bitch Feminism: Blackfaced Girlboss in Feminist Performative/Performativity Politics”(第1章)探讨“白人对Bitch的再占有如何延续了反黑人性”,以及“通过Bitch表演性来为女性主义‘世界化’如何通过加固‘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来使性别分析变得可理解”。本章考察Bitch表演性的三个关键文本:Joreen(Jo Freeman)于1968年撰写的The Bitch Manifesto;2013年的病毒式恶搞短片“Bitchy Resting Face”;以及Tina Fey联合制作的喜剧《Great News》(2017–18)中的“boss bitch”角色。这些文本主张应当“再占有Bitch”,因为被标为“bitch”的人拒绝“被奴役”;她们比那些“屈从于Womanhood”的女性更mean、更聪明。基于我对Joreen之“enslavism”的解读——其灵感部分源自她对参与民权运动的黑人女性的“嫉妒”——以及“黑性如何在‘Bitchy Resting Face’与《Great News》中被作为‘酷’的策略来部署”,我探讨“Bitch之再符号化政治”如何构成一种“blackface”:它摹拟一种“被剥权的、抵抗性的表演性”,同时拒绝“黑人群体之合法性”。我主张:Bitch女性主义中的“白人bitch”被发明为“更好的主人”,因为她可以通过“bitch her way”穿行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作为她自己,同时作为主人本人”。
除了因其“抵抗潜力”而庆祝mean girl形象之外,女性主义也将mean girl塑造成“特洛伊木马”,以巩固“女性主义与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之间需要一种对立关系”的必要性。mean girl形象体现了“被种族化的愤怒”,却对“后父权时代应当何为”语焉不详。“Mean Girl Feminism: Gatekeeping as Illegible Rage”(第2章)探讨“愤怒与meanness如何形塑媒体研究中的女性主义”,尤为关注电影《Mean Girls》(2004)中的mean girl母题。我考察女性与mean girls如何被视为“阻碍女性主义政治进展的后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让“女性团结”难以成立,并最在乎“将自己与他人暴露于异性恋规范的男性凝视”。女性主义给出的对付mean girls之“解方”与其“后女性主义变体”实则同出一辙:通过“将身份重新指向‘将压迫源头归于性别’的女性主义原则”,为白人女性的愤怒寻找“富有生产性的释放出口”。在探究“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如何遵循德里达式的‘增补’逻辑”时,我主张:女性主义对后女性主义的“指控”,通过重复将自身表述为“生成独特之社会与政治欲望与结果”的话语,劈裂并延缓了女性主义之“抵达”。为将女性主义与后女性主义区分开来,女性主义研究也动用“mean girl母题”,从而生产出一个二元:白人mean girls(使女性主义对话变得不可能的后女性主义替罪羊)vs. 白人“nice girls”(文明、礼貌的女性主义者,她们被阻止明确阐述女性主义政治)。通过将自己置于“meanness逻辑”之外,白人“nice girl”女性主义者(如《Mean Girls》中的Cady)被塑造成“更好的主人”,因为她们不是meanness的起源,即便她们开场(并暴露)了它。
“权力伴侣”(power couple)的建构,通过将本应面向“共同体工作”的策略与感情转而用来建设“志同道合的小团体、伴侣关系与家庭”,将女性驯化为“支持丈夫的淑女”。其结果是,“权力伴侣式女性主义”鼓励的不仅是她的“个体成功”,更是他们“作为顺性别异性恋伴侣的成功”。通过分析若干涉及mean girls与女性浪漫追求的近期媒介文本,“Power Couple Feminism: Gaslighting and Re-Empowering Heteronormative Aggression”(第3章)考察“白人异性恋之爱如何被建构为一个‘可拯救白人’的女性主义领域”。“power couple”一语标记了“女性主义对白人异性恋婚姻安排的正向影响”。我主张,“权力伴侣式女性主义”保护“暴力男性”,并遮蔽“帝国主义白人至上资本主义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暴力,以展示一种“女性主义式的工作—生活平衡”。在“权力伴侣式女性主义”中,“暴力白人男性”显得“可爱”,“白人mean women”则以“其救赎者”形象获赎。“热爱白人攻击性男性气质”的白人mean girls并非不受伦理评判、亦非从伦理中解脱:她们的伦理恰恰由“维护白人异性恋家庭价值”所构成。“权力伴侣式女性主义者”是一种“更好的主人”,因为她自称能用她的“爱”来“管理白人男性之暴力”。
随着“性别平等”的普及,女性主义成为“诸多机构”的一部分,而这些机构有意通过专家与管理者(如今成为官僚运作的一环)来“合法化其权力与政策”。正如Raka Shome关于“全球母职”所述:“只要能被置于某些国家霸权的服务中,白人女性性就可以为国家所用。”85 “Global Mother Feminism: Gatekeeping Biopower and Sovereignty”(第4章)探讨“政治保守女性如何以与自由女性主义价值与承诺相容的方式来表演‘全球母职’”。自由女性主义者更关心“白人女性进入政治”,较少关注“她们的政治对有色人群的影响”,因此主张“第一夫人劳拉·布什与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也是女性主义者”;这一论断搭建于“布什将白人女性主义价值用于支持美国占领阿富汗的倡议”,以及“佩林在媒体中所面对的‘基于性别的审视与性别歧视’”之上。我选择“温和、友善仪态”的布什与“以政治锋芒著称的mean girl”佩林,以展示“流行女性主义如何从‘政治规约’转向‘由全球母职所体现的表演性政治’”。本章主张,女性主义“弱化其对于白人政治保守女性的对立”,以“缓解政治性的embourgeoisement”,并保留在“治术中对‘照护与生活品质’作出裁断”的能力。“全球母职女性主义者”是一种更好的主人,因为她将“白人的生命政治(biopower)”嵌入“性别化的利益与纳入”。
通过将“性别化表演”作为“斗争”,并扩张“白人异性恋—女性化表演”之谱系作为“女性主义的”,女性主义抹除了自身作为一种“戏弄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并重申殖民主权”的“文明性形式”的暴力。在结论“Abolishing Mean Girl Feminism”中,我将考察由被种族化女性实施的多种meanness实例,以显示“被种族化的meanness在大众文化中如何以不同方式运作”。我将思考一种“去殖民/后殖民的女性主义”,来挑战“文明性政治”。
我对本书的期许,并非“取消女性主义这一宏大工程”,而是检视“促生meanness成为‘殖民主权之情感形态’的‘表演性转向’”。如同《最蓝的眼睛》中的克劳迪娅(Claudia)——艾哈迈德将其描述为“黑人女性主义的扫兴者(killjoy)”,“她‘利用(一个白人娃娃的)礼物来生成反知识’”——我希望“利用女性主义这一礼物”,来生成关于“white feminism如何将自身部署为一种‘排斥有色女性’的抵抗形式(即便它声称纳入她们)”的新理解。86 这一“双重动作”在人们的轶事经验中耳熟能详,但尚未被分析性地考察为“出自女性主义自身”的现象。
通过探究“女性主义如何将mean白人女性主人公确立为‘父权的问题’与‘非暴力的进步征兆’”,本书展示“表演性如何为‘白人女性主义之承认政治’的不安与不稳提供屏幕”。mean girl 女性主义将“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的压迫”,简化为“处于善于言辞的女性主义者之掌控与舒适范围内的’交往互动与表演体’”。以此方式来“常态化与性别歧视的对峙”,阻滞了对“父权压迫与其他权力体系交叉处”的扎实介入。“表演性转向”不仅服务于新自由主义目标(主体将“真实性与自由自我表达”视为成功抵抗权力的标志),也服务于殖民利益(将暴力分散到那些一方面向内反思“性别压迫”、另一方面将其反叛以“人际方式对外化、且无方向也无需担责”的主体之上)。转向“表演性”(如何行动、穿什么、如何举止),让女性主义得以将自身重新对齐为“打断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而非“想象新的集体自由形式”。女性主义的文明性对有色人群施以“煤气灯操纵”、替“愤怒把门”,并以“girlboss之姿”筹划一个在顺性别-异性恋父权制中“为白人女性保留特殊位置的未来”;然而这些愤怒本可被升华为“集体解放”。
注
1. 关于该音乐录影,请参见 “Taylor Swift- Mean,” YouTube video, posted May 13, 2011, by Taylor Swift, 4:03, www.youtube.com/watc....
2. 关于霉霉将“girl power”作为女性主义运用的一则简短讨论,参见 Camille Paglia, “Camille Paglia Takes on Taylor Swift, Hollywood’s #GirlSquad Culture,” Hollywood Reporter, December 10, 2015.
3. 我使用“girl”这一术语,遵循 Marina Gonick 对新自由主义中的“girl power”文化的理论化:该文化将“女孩”表述为“自我决定个体的理想化形式”,以与女孩在早期心理发展阶段的自尊匮乏、失语与脆弱形成对照。Gonick 指出,关于“白人中产阶级女孩期”与“恰当女性气质”的焦虑,会被指向青春期女孩,也会被指向成年女性。Marina Gonick, “Between ‘Girl Power’ and ‘Reviving Ophelia’: Constituting the Neoliberal Girl Subject,” NWSA Journal 18, no. 2 (2006): 1–23. 另参见 Jessica Ringrose, “A New Universal Mean Girl: Examini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Regulation of a New Feminine Pathology,” Feminism & Psychology 16, no. 4 (2006): 405–24; Deirdre M. Kelly and Shauna Pomerantz, “Mean, Wild, and Alienated: Girls and the State of Feminism in Popular Culture,” Girlhood Studies 2, no. 1 (2009): 1–19. 同时,我也注意到,“niceness”同样被规定为恰当女性气质的表演要件,参见 Laurie A. Rudman and Peter Glick, “Prescriptive Gender Stereotypes and Backlash toward Agentic Wome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7, no. 4 (2001): 743–62.
4. Koa Beck, White Feminism: From Suffragettes to Influencers and Who They Leave Behind (London: Simon and Schuster, 2021), 178.
5. 我依循 Ruby Hamad 及诸多学者,将“white womanhood”用作分析之概念,强调其作为一种排他性的构造,意在界定“谁才算是女性”。Hamad 解释说:“这与阴性与阳性、以及一个人应如何行为以被充足地归入其一并无关,而在于谁算作女性,谁算作男性。谁算作人。”Ruby Hamad, White Tears/Brown Scars: How White Feminism Betrays Women of Color (New York: Catapult, 2020), 124. 在力图对抗这种排他性的同时,我亦遵循 Sara Ahmed 对女性主义的界定,即“在这个世界上支持女性为生存而斗争”,这意味着支持“一切行进于‘women’这一能指之下的人”。Sara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6. Vinay Menon, “Mainstreaming of Mean: Our Age of Nastiness, Deceit, and Malice,” Toronto Star, November 15, 2013.
7. Melissa Gregg, “On Friday Night Drinks: Workplace Affects in the Age of the Cubicle,” in The Affect Theory Reader, ed. Melissa Gregg and Gregory J. Seigwort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50–68.
8. Soraya Roberts, “‘Mean’ People Top Forbes’ List of Top-Earning Media Personalities,” Yahoo News, November 4, 2014, news.yahoo.com/.
9. Gerald A. Voorhees,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 in Mass Effect: The Government of Difference in Digital Role-Playing Games,” in Dungeons, Dragons, and Digital Denizens: The Digital Role-Playing Game, ed. Gerald A. Voorhees, Joshua Call, and Katie Whitlock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2012), 259–77.
10. Ann Laura Stoler, 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6–37.
11. See Gabrielle Moss, “Teen Mean Fighting Machine: Why Does the Media Love Mean Girls?,” in BITCHfest: Ten Years of Cultural Criticism from the Pages of Bitch Magazine, ed. Lisa Jervis and Andi Zeisl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6), 43–48.
12. Hélène Cixous,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Signs 1, no. 4 (1976): 875–93.
13. Sheryl Sandberg, 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 (New York: Alfred Knopf, 2013); and see Beck, White Feminism, 193.
14. Sally Kohn, “Affirmative Action Has Helped White Women More Than Anyone,” TIME, June 17, 2013.
15. 我借用 Stoler 的术语“white prestige”,用以指称那些已属或试图成为资产阶级之主体的白人特权。有时,我将其与“white privilege”互换使用。
16. Beck, White Feminism, 215.
17. Robyn Wiegman, American Anatomies: Theorizing Race and Gende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7.
18. Hamad, White Tears/Brown Scars, 130–32.
19. Rebecca Traister, Big Girls Don’t Cry: The Election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for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2010), 272.
20.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160, 174.
21. Alexander Weheliye, Habeas Viscus: Racializing Assemblages, Biopolitics, and Black Feminist Theories of the Hum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26.
22.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203.
23. Jay Dolmage, Academic Ableism: Disabilit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7).
24. Sara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35.
25. Jessie Daniels, Nice White Ladies: The Truth about White Supremacy, Our Role in It, and How We Can Help to Dismantle It (New York: Seal Press, 2021), 50.
26. Hamad, White Tears/Brown Scars, 101.
27. Sara Ahmed, “The Nonperformativity of Antiracism,” Meridians 7, no. 1 (2006): 105. See also Michelle Daigle, “The Spectacle of Reconciliation: On (the) Unsettling Responsibilities to Indigenous Peoples in the Academ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7, no. 4 (2019): 703–21.
28. 对我而言,“performative turn”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政治中的“embodied turn”,尽管二者相关。关于将具身政治视作表演性的讨论,参见 Natalie Fixmer and Julia Wood, “The Personal Is Still Political: Embodied Politics in Third Wave Feminism,” Wome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28, no. 2 (2005): 235–57.
29. Daniels, Nice White Ladies, 8.
30. See, respectively, Laura Kipnis, “(Male) Desire and (Female) Disgust: Reading Hustler,” in Cultural Studies, ed. Lawrence Grossberg, Cary Nelson, and Paula Treichl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73–91; Wendy Brown, 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Louise Michele Newman, White Women’s Rights: The Racial Origins of Femi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Kyla Schuller, The Trouble with White Women: A Counterhistory of Feminism (New York: Bold Type Books, 2021); Jack Halberstam, “You Are Triggering Me! The Neo-Liberal Rhetoric of Harm, Danger and Trauma,” Bully Bloggers (blog), July 5, 2014, bullybloggers.wordpr....
31. Mamta Motwani Accapadi, “When White Women Cry: How White Women’s Tears Oppress Women of Color,”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Journal 26, no. 2 (2007): 210.
32. Ann Laura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Gender, Race, and Morality in Colonial Asia,” in The Gender/Sexuality Reader: Culture,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ed. Roger N. Lancaster and Micaela di Leonardo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9.
33. Stephanie Jones-Rogers, They Were Her Property: White Women as Slave Owners in the American South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4. W endy Anderson, Rebirthing a Nation: White Women,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 (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2021), 12.
35. Shawn Michelle Smith, American Archives: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Visual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4.
36. Elizabeth Gillespie McRae, Mothers of Massive Resistance: White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hite Suprem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
37. Hamad, White Tears/Brown Scars, 14.
38. Schuller, The Trouble with White Women, 4.
39. Laura Kipnis, The Female Thing: Dirt, Sex, Envy, Vulnera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6), 5 (qtd.), 7.
40. Beck, White Feminism, 118.
41. Newman, White Women’s Rights.
42. Beck, White Feminism, 29.
43. Angela Davis, Women, Race, &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3); Barbara Ehrenreich, “Maid to Order,” in Rhetorical Vision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a Visual Culture, ed. Wendy S. Hesford and Brenda Jo Brueggemann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2007), 427–38.
44. Therese Saliba, “Military Presences and Absences: Arab Women and the Persian Gulf War,” in Seeing through the Media: The Persian Gulf War, ed. Susan Jeffords and Lauren Rabinovitz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263–84.
45.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Boston: Beacon Press, 2018), 137.
46. Vron Ware, Beyond the Pale: White Women, Racism, and History (London: Verso, 1992), 37.
47. See Stoler, “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48. Penelope Edmonds, “Unpacking Settler Colonialism’s Urban Strategies: Indigenous Peoples in Victoria, British Columbia, and the Transition to a Settler-Colonial City,” Urban History Review 38, no. 2 (2010): 12.
49. Ann Laura Stoler and Frederick Cooper, Tensions of Empire: Colonial Cultures in a Bourgeois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31.
50. For how space can be coded as white, see Setha Low, “Maintaining Whiteness: The Fear of Others and Niceness,” Transforming Anthropology 17, no. 2 (2009): 79–92;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3, no. 3 (2011): 54–70.
51. Cecily Jones, “Contesting the Boundaries of Gender, Race, and Sexuality in Barbadian Plantation Society,” Women’s History Review 12, no. 2 (2003): 224.
52. Schuller, The Trouble with White Women, 8.
53. 参见(依次):Erin Rand, Reclaiming Queer: Activist and Academic Rhetorics of Resistance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4); Sara Ahmed,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4.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74, 52. 关于“无法律之领域”的可能性,以及“法律之背面如何依赖于非法律之例外状态的生产”,在 Agamben 的工作中被否认,正如 Alexander Weheliye 所精彩阐明者;see Weheliye, Habeas Viscus.
55. Benet Davetian, Civility: A Cultural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9), 29.
56. Davetian, 355. 在 Davetian 处,“rudeness”是“文明性”的一个类别,可被用来抵抗“地位与权力的表演”,或抵抗那些“限制不平等议题讨论的话语惯例”。
57. T avia Nyong’o and Kyla Wazana Tompkins, “Eleven Theses on Civility,” Social Text (website), July 11, 2018, socialtextjournal.or....
58. Schuller, The Trouble with White Women, 9.
59. Ahmed,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32.
60. Daniels, Nice White Ladies, 47. Daniels 说明:白人女性的“无辜与脆弱”搭建起“友善”的门面,却可能给被种族化人群带来危险。当白人女性“收起”meanness 时,她们恰恰展示了体制如何为她们自身、也为他人“良好运作”。
61. Lauren Berlant, The Female Complaint: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Sentimentality in American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9.
62. See Ronald Walter Greene, “Rhetoric and Capitalism: Rhetorical Agency as Communicative Labor,”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37 (2004): 188–206; Toby Miller, The Well-Tempered Self: Citizenship, Culture, and the Postmodern Subjec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63. W eheliye, Habeas Viscus, 3.
64. Wiegman, American Anatomies, 97; see also Jessie Daniels, White Lies: Race, Clas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White Supremacist Discours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64; Jacquelyn Dowd Hall, Revolt against Chivalry: Jessie Daniel Ames and the Women’s Campaign against Lynch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关于 The Birth of a Nation,bell hooks 指出:“自《一个国家的诞生》起,种族与性别政治便被铭刻进主流电影叙事之中。这部开创性作品界定了白人女性在电影中应当占据的地位与承担的功能。” in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y bell hook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2), 119–20.
65.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132.
66. Beverly Tatum 指出:“62% 的无大学学历白人女性投票支持特朗普,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女性亦有 45% 如此投票。”Beverly Tatum, Why Are All the Black Kids Sitting Together in the Cafeteria? And Other Conversations about R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7), 64. Wendy Anderson 同样解释,白人女性支持“白人民族主义”:“白人民族主义者挪用‘女性主义’、‘厌女症’、‘性别歧视’、‘边缘化’、‘修正主义’及‘另类声音’等术语,颇具讽刺意味地为其所谓白人遭受边缘化的主张提供依据。” Anderson, Rebirthing a Nation, 58.
67. Sylvia Wynter, “Beyond Miranda’s Meanings: Un/Silencing the ‘Demonic Ground’ of Caliban’s ‘Woman,’” in Out of the Kumbla: Caribbean Women and Literature, ed. Carole Boyce Davies and Elaine Savory Fido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1990), 355–72.
68. Sylvia Wynter, “Unsettling the Coloniality of Being/Power/Truth/Freedom: Towards the Human, after Man, Its Overrepresentation—An Argument,” CR: 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 3, no. 3 (2003): 260.
69. Rafia Zakaria, Against White Feminism: Notes on Disrup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21), 16.
70. Sabi, Broeck, Gender and the Abjection of Blacknes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8), 5; see also Ware, Beyond the Pale, 57, 107.
71. Broeck, Gender and the Abjection of Blackness, 55.
72. Davis, Women, Race, & Class, 33–34.
73. Karen Sánchez-Eppler, “Bodily Bonds: The Intersecting Rhetorics of Feminism and Abolition,” Representations 24 (1988): 29, 31, 33; see also Shirley Samuels, The Culture of Sentiment: Race, Gender, and Sentiment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7.
74. Sylvia Wynter, “Do Not Call Us Negros”: How “Multicultural” Textbooks Perpetuate Racism (San Francisco: Aspire Books, 1990), 13.
75. Davis, Women, Race, & Class, 111–14. 此外,Davis(142)指出,Susan B. Anthony 的女性主义是“embourgeoisement”的一种体现:“Anthony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鲜明映照。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蒙蔽作用,使她未能认识到:在并无性别之分的阶级剥削与种族压迫之下,工人阶级女性与黑人女性本质上都与本族男性结成了根本纽带。”
76. Davis, 210.
77. Davis, 121, 229.
78. 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 (1989): 139.
79. 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19.
80. Saba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See also Barbara Biesecker, “Coming to Terms with Recent Attempts to Write Women into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Philosophy & Rhetoric 25, no. 2 (1992): 140–61.
81.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9.
82. Mahmood, Politics of Piety, 18.
83. Eve Tuck and K. Wayne Yang, “Decolonization Is Not a Metaphor,” Decolonization: Indigeneity, Education & Society 1, no. 1 (2012): 3.
84. Sara Ahmed, “A Phenomenology of Whiteness,” Feminist Theory 8, no. 2 (2007): 149–68.
85. Raka Shome, Diana and Beyond: White Femininity, National Identity, and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4), 73.
86. Ahmed, Living a Feminist Life, 41.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