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村九皇爷诞歲月

小时候,新村小孩有两件人生大事:新年十五天,九皇爷诞九天。想逃?没门。逃了就等于跟全村绝交。
婆婆最虔诚,天还没亮就冲去庙里拜神。回来手上总多几条黄色布条,还带着签言。她把布条往我手腕一绑,嘴里念念有词,好像在给小鸡打成长激素:“快高长大,健健康康。”我那时傻呼呼的,还抬头问:“要戴多久?”婆婆当然不会回答,她哪里懂什么“用户协议”?反正就是戴到它自然掉为止。掉了,就算神明撤资,平安要另购保险。
上学后,看见同学没布条,我心里酸酸的,还偷偷塞一条给他。他摇摇头:“妈妈不给戴。”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做好事,而是在走私,手上攥的不是布条,是违禁品。第二年我又长高了,坐到最后一排,他还在前排。我心里还算命似的想:要是当时戴上布条,不就能坐我旁边?结果被老师派去擦黑板,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今天。
婆婆不让我进庙,人太多,怕走丢。但戏台一定带我去,还得一早霸位。台上唱福建戏,我一句听不懂,却非要拉着婆婆问剧情。婆婆顾不上我,她已经彻底沉浸,眼睛比探照灯还亮,表情一套套切换,比演员还快。我抬头看她的脸,就像看字幕:婆婆的表情,就是我理解戏曲的翻译。
等到十二、三岁,庙会的意义终于升级。我跟朋友学泊车童,手电筒一照,往车位一指,摆出一副专业样子。有人付钱,有人赖账。我们小孩也不怕,被赖了就心里默默念:等你走远了才放风。零钱分赃,买花生,蹲在马路边嘎嘣嘎嘣啃,自以为古惑仔少年团。庙会明明是神圣仪式,被我们硬生生玩成江湖试炼场。
游行队伍才是庙会高潮。接神、送神,桥轿抬起,舞龙舞狮,白衣黄巾的信徒赤脚跟上,还有乩童。秩序我是没办法顺着讲,混在里面根本数不清。直到后来玩摄影,我才学会当个旁观者。
中学时认识一个同学就是乩童,个子不高,很瘦小。有时扮三太子,有时扮大圣爷。我一认出来非常激动,硬要他教我。他开出来的条件我立刻打消念头:要吃斋,还要禁女色。吃斋还可以接受,禁女色就算了,人家还是处男。
最震撼的是过火炕。印象中有一次,我排着队想走,师傅一看我吓得脚抖,挥手拦下。后来听朋友吹,说不烫什么的,声音越讲越大,我心里越懊恼——当时怎么那么胆小?
不过电视儿童有电视儿童的补偿机制。过火炕也好,禁女色也罢,没参与到也不会太遗憾。毕竟奥特曼、蜘蛛人关掉电视照样要写功课,永远也变不了身。九天过后,一切恢复原状。外星人、UFO、神秘失踪的MH370——都一样保持着信而不迷的态度。
庙会年年相似,人年年不同。回过头才发现,婆婆绑在我手上的那条黄色布条没骗我:瞬间已长大成中年大叔了。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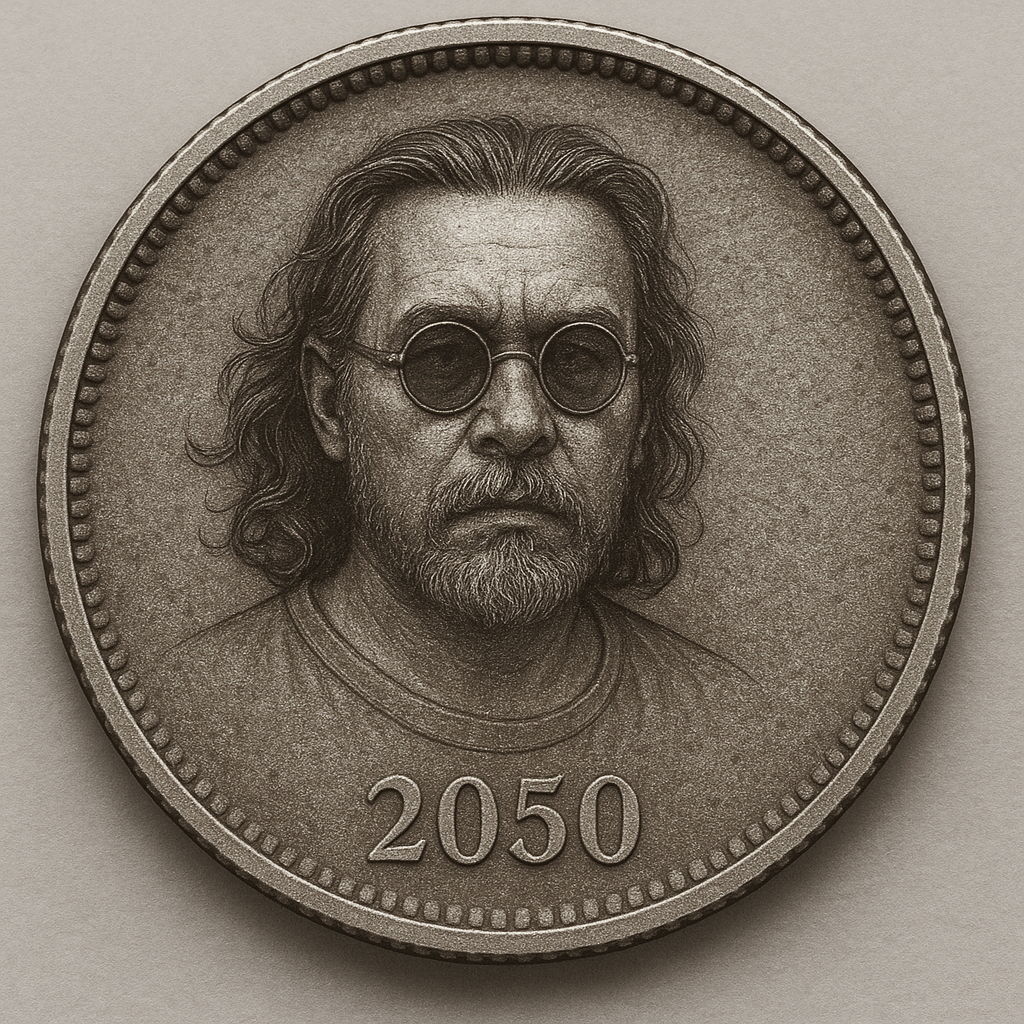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