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記框架表決在即 同志群體中的「非主流」 仍待被看見的多元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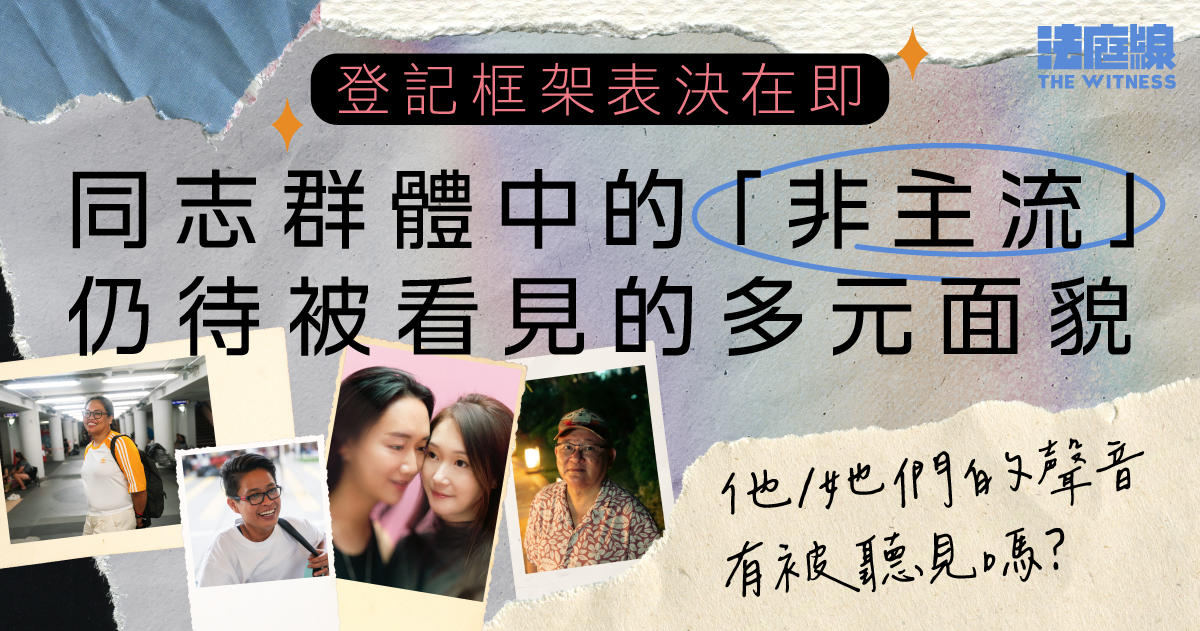
政府提出《同性伴侶登記框架條例草案》,旨為履行終審法院 2 年前的判決,確立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法律承認,以保障其《人權法案》下私生活的權利。
法案正於立法會審議,反對聲眾。有議員認為制度變相承認同性婚姻,衝擊現有制度;有人擔心主流社會未能接受;亦有少數議員關注,制度有助提升香港開明包容形象,認為應尊重法院判決。
被司法覆核申請人岑子杰形容為對權利闡述「超出想像」地低的框架,在議員間掀起波瀾,何況議事堂外的世界,真實人群的面貌本就千百種。在被視為非「傳統」、非「大多數」的同志之間,還有更「少數」、更「非主流」的一群。性小眾身分與不同性別、年齡、社經地位等交織,各人際遇、需要自有不同。現時討論的一紙框架,又能否對應他 / 她們的境況?
《法庭線》分別採訪了跨性別女同志、年長男同志、以及移工女同志,嘗試探問他 / 她們日常在經歷甚麼?如果登記制度非一勞永逸,社會可抱持怎樣的想像,才有機會真正看見、回應多元社群?跨性別女同志 / Ming 與 Carmen
「我們在 living out 一種 possibility」

今年 29 歲的 Ming 和 30 歲的 Carmen,分別是醫生及空中服務員。
訪問當天是周末早上,兩人結伴前來,聽從攝影師建議,身穿相襯的黑上衣配藍色牛仔褲,輕快地踏入咖啡店赴約。
正式訪問前,我們閒談起,她們訪問完結後要去購買下周泰國旅行所需物品,晚上要回娘家吃飯⋯⋯
這樣看來,Ming 和 Carmen 跟香港大部分關係穩定的情侶,沒甚分別。
出櫃「可能其實 not a big deal」
Ming 是跨性別女性,Carmen 是順性別女性。兩人 3、4 年前網上認識,後來相戀。第一次在咖啡室見面,坐的碰巧是訪問當天的位置。
Ming 讀大學第二、三年級時開始性別過渡。當時因讀醫壓力大,去見輔導員,順道談到自己的性別認同,輔導員建議,不如跟系內相關教授談一談。
「我以前一路覺得 transition (性別過渡)係唔可行嘅,因為又要食藥又剩⋯⋯我又比較細膽,覺得好似要好大改變、好大風險咁。」
教授聽完她的狀況,徐徐一句,「佢話:『我覺得個樣做女仔都 okay 吖』,『我幫你寫(轉介)信啦。』」
從容的語氣,令她意識到,「其實我係可以有自己選擇,同埋令我明白,其實可能真係 not a big deal(沒有甚麼大不了)。」

她回想起當年出櫃,除了母親「眼濕濕」,長年在內地工作的父親、和身為基督徒的姐姐的反應,也超乎她意料地平淡。
「我老豆完全無嘢,佢話,你係認真嘅,咪去做囉!」
和姐姐出櫃的對話,前後不超過 10 句,「我話,『我係 transgender(跨性別)』,佢就『哦』;我話,『我開始食緊荷爾蒙啦』、『你有無咩問題啊?』佢話:『無啊』。就係咁樣。」
「呢部分我係超好彩嘅。」
Carmen 則說,認識 Ming 之前,自己已認同為雙性戀者,但以前交往的對象都是男生,後來覺得還是和女生一起比較合適。男女關係中對性別刻板定型和期望也叫她不舒服。
「譬如你去對方屋企食飯,通常女仔第一次都要『扮』洗碗,但調返轉就好少會 expect(預期)個男仔要洗碗。」
Carmen 開始在交友程式中認識不同女生,遇上了 Ming,被她的幽默感吸引。
「例如我講啲鳩嘢、或者 meme(迷因)啲嘢,她知道我講乜」,她又喜歡 Ming 的真誠,「她個人比較直接,相處上都舒服,我唔鍾意啲人包裝太多」。

婚姻的意義?
交往兩年後,兩人開始討論結婚,並於 2023 年經美國猶他州網上註冊。
本港現行政策規定,跨性別人士要申請更改身份證性別,至少須完成手術切除性徵。未完成手術的 Ming,身份證上的性別仍顯示為「男性」,BNO 護照則已改為「女性」。
換言之,即使同性伴侶登記制度能通過立法,Ming 和 Carmen 仍不屬條文下定義的「同性」伴侶。
另一邊廂,在香港「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下,她們理論上可到婚姻註冊處註冊,但這不是她們的選項,「因為我唔想係先生、我唔想係丈夫。」Ming 說。
二人仍然年輕,經濟狀況亦穩定,住屋、醫療、繼承等暫非眼前最擔心的問題。結婚對二人最大的意義,是婚書背後的承諾。
Carmen 說,認識 Ming 之前,已厭倦和前男友們分分合合,就算當時認識不同女生,均開宗明義以結婚為前提。
「我想要一段關係,係有咩問題大家一齊解決,而不是去逃避。」
認識 Carmen 之前,Ming 也才 20 多歲,有好幾年時間都在探索,有過不少短暫關係,「慢慢開始想揾一個人,可以同我一齊經歷、一齊去承諾。」
不過人生路漫長,雖然二人暫時無意養育小朋友,但也想像過,萬一日後改變主意呢?
「我哋都有討論過,話呢件事只能夠係我哋去咗英國、移咗民,先可以。」Carmen 斬釘截鐵,「因為香港實在太複雜喇,我哋連自己本身肯定身分都做唔到,更加唔好講有下一代、或者領養。」
性別捆綁
二人順利在海外成婚,但向親朋戚友交代,才是最大考驗。
雙方直系家庭一直相當接納她們,但對著老一輩或關係較疏的親戚,仍難以解釋;部分親戚就算暗地知道狀況,也會怕尷尬而不明言。
兩人結婚時是疫情尾段,因人數限制未有邀請太多人觀禮,也未有大排筵席,之後才跟親友吃一頓飯慶祝。
吃飯當晚,為免被問長問短,Ming 不穿胸圍、不化妝、穿上男裝襯衫,面對大群首次見面的親戚。
「因為驚萬一有一個人唔 okay,唔係淨係我哋難受,佢(Carmen)屋企、佢阿媽都會好尷尬。」
為體貼別人感受,選擇委屈自己。不過那晚到最後,Ming 還是忍受不了,悄悄放下本來束起的頭髮。
Carmen 親戚是客家人,新年習俗要在圍村中庭吃盆菜,已婚的要向全村人派利是,Carmen 不敢想像,若 Ming 不是以沒有假期為藉口,避過回去拜年的話⋯⋯
「成條村,不停『你老公⋯你老公⋯』咁叫⋯⋯」Carmen 苦笑,「簡直係行刑咁。」

遊走於邊沿
Ming 說,開始性別過渡之後,身邊同學、朋友,甚至工作機構,大體上對性小眾友善。但身為跨性別女同志,無論是在主流社會、抑或 LGBT 群體裡,她仍然遊走於邊沿。
例如在女同志交友平台 Butterfly 上,不少群組會標明歡迎入群的女同志類別,譬如說只限「TB 和 TBG」、「Pure」【註】等加入。
Carmen 解釋:「但通常都會標明『no men(不接受男性)』,或者要你影相、錄音,去證明你係 cis-woman(順女性)」
Ming 說,即使是同志圈裡,亦有不少人恐跨,「有啲人會覺得,總之你未做手術,你就根本係男人啦!然後當你講啲性別理論,佢拗唔過你,就會話:你啲咁 advance(進階)嘅嘢無用㗎!香港係唔會有改變㗎!」她苦笑,「但問題係,好似你自己本身都係個小眾?」
令她覺心痛的,是有時會看見有跨女在平台上發言,會因自己未完成整套手術,「就話,『我都唔想話自己係女人啦』,意思即係,咁你憑咩話自己係女人呢?」
「佢哋內化咗果種邏輯,寧願犧牲自己,都要去維護呢個規則,我就覺得,哇⋯⋯好 sad(可悲)」
雖說社會較從前進步,但主流對性別、婚姻仍存不少僵化想像,登記制度在立法會也阻力重重,遑論如何保障跟 Ming 和 Carmen 類似、更難被主流看見的群體。
至於支持平權一方,不少團體傾向支持登記制度立法。Ming 說可以理解大家想「袋住先」,但「有啲似係,大家會記得有 LGB,但未必記得 T 嘅存在,我係有少少無奈。」Ming 說,遑論是次的框架,對同性伴侶保障也相當有限。
登記制度以外,對 Ming 和 Carmen 而言最重要,是香港在性別承認議題上,還能走多遠?
「在我哋個 case,係需要先承認(Ming 的女性)性別,先可以認可我哋外國份婚姻證書 ,如果唔係,雖然我哋結咗婚,喺香港都係無效。」Carmen 說,「但我覺得,而家佢哋連登記都搞到咁複雜,係咪可以走到咁前呢?我係比較悲觀嘅⋯⋯」

狹縫生花
不平凡的一對,身處主流框架的狹縫中,日常仍然面對不少掙扎。
Ming 表面開朗健談,但有時狀態不佳,仍會對身體或嗓音不滿意,致性別不安來襲。
Carmen 則每次出勤,同機空中服務員休息時閒聊,常談到伴侶、家庭話題。其中一次同事聽到 Carmen 的伴侶是跨女,拋下一句,「佢未做手術㗎嘛,咁你鍾唔鍾意 jer(陽具)呀?」
「我嗰下係呆—撚—咗啦」Carmen 說,「跟住我都冇出聲,話我要出去同個客講嘢,避咗件事。」
Ming 說,有些人覺得,彷彿談到跨性別人士,就突然有權隨便談論別人的性器官。「我知道咁講好老土,但其實真係,我哋係咪都可以唔同意、但互相尊重呢?」Carmen 補充。
「我哋存在,就係存在,我哋唔會因為你唔同意就分解、消失。」
訪問過後,攝影師為二人拍攝,她們的表情由最初緊張生硬,慢慢放鬆下來,時而細心為對方整理頭髮,時而互相捉弄嬉鬧,笑得嘻嘻咔咔。
「我哋做一齊、結婚嘅決定嘅時候,我係無考慮到人哋點睇我哋,就只係好自然咁去做。」
Ming 說:「但有時當我睇返個社會,我又覺得,好似我哋嘅存在,係 living out 一個 possibility (活出一個可能性)畀其他人睇。」
【註】TB 意指偏陽剛打扮的女同志,TBG 指喜歡 TB 的女同志,通常外觀較女性化;Pure 意指外觀上較女性化、亦喜歡同樣女性化的女同志。
67 歲男同志 / Lucas
與伴侶共度 32 年、去年成婚

Lucas 和伴侶同居逾 20 年。有件事,曾令他介懷。
當時還住在美孚舊居,他和伴侶、伴侶的媽媽和姐姐,4 人生活在一個小單位,方便照顧。一次閒聊,姐姐說:「如果第日細佬結婚呢,佢老婆喺度,我哋就要搬走喇。」一直很疼 Lucas 的伴侶媽媽,沒有作聲。
「我當時係有少少唔開心嘅,」Lucas 說,「唔知係咪佢唔想接受呢個現實呢?即係佢覺得,你哋係好兄弟咋嘛。」
「但我覺得⋯⋯你都唔係盲㗎啦,我哋一齊咁多年,瞓埋一張床咁多年,你仲可以咁講嘅?」
九十年代相識 異地相戀10年
Lucas 今年 67 歲,出生及成長於新加坡,1991 年來港公幹,翌年認識了現在的伴侶。
「成 32 年!可能你哋未出世我哋已經一齊喇!」Lucas 望著年紀比他小一大截的記者,爽朗地笑。
那是科技、性別意識都不如今天的年代,影視作品還常帶歧視同性戀的內容。但 Lucas 記得,當年香港已有好幾間同志酒吧,成為不少人聚腳交友的地點,他倆也在酒吧相識。
「無 Apps 啦以前!」他笑指,「(那年代)你話係咪好保守⋯⋯通常就係你唔問,我就唔講囉,同埋都唔同屋企人講㗎嘛。」
現已是六旬叔叔,相識時,兩人不過 20、30 出頭的壯年人。Lucas 最初從新加坡來港,「我係好 westernized(西化)嘅,未嚟香港之前唔係好識講中文,但佢就係講廣東話,咁就逼住我不停咁講廣東話啦。」
伴侶從小在香港長大,受華人文化影響,較壓抑自我。「佢壓力大過我,所以佢都會怕、會擔心人哋點睇。」

Lucas 從事酒店業,以前常要飛不同地方,關係開始一年,他先後到日本、英國等地公幹,一直靠長途電話和傳呼機維繫。
交往頭幾年,Lucas 在日本,兩人每晚都講上半小時電話,才捨得睡覺,「你諗下啲電話費幾貴!」
接近 1997 年,加上新加坡經濟起飛,開放移民政策吸引外資,Lucas 替伴侶申請移民新加坡,但對方放不下香港的家人,拖了又拖。
關係再添波瀾,兩人一度擔心走不下去。
最後 2003 年沙士後,「我覺得要做一個決定喇,佢唔過嚟新加坡,咁我就決定搬嚟香港住。」並買了單位同居。
Lucas 說,他倆都是事業心重的男人,各自在不同城市打拼,交往頭 10 年聚少離多。每次遠道探望對方,都格外珍惜相聚的時間。
「喺埋一齊嘅時間少,就唔會計較太多嘢,唔會咁執著。」他分享相處之道,「一定有啲拗撬,但過咗就無嘢㗎啦,唔會記仇囉⋯⋯」
香港 1991 年男男同性性行為除罪化,新加坡至 2022 年,才廢除禁止男性同性性行為的刑法條文。
Lucas 說,雖然新加坡法律上走得慢,但社會、文化上,對同性戀態度很早已相當開放。Lucas 14 歲結交第一個男朋友,少年時也未曾遭遇任何欺凌、歧視。
「雖然法律上唔接受,但好彩我屋企人都好接受,好 open(開明)。」
「佢好早已經係我屋企一部分,我所有啲細佬結婚啊,侄仔、侄女出世,都有請佢過去參加,個個都知道佢係我 partner(伴侶),屋企有啲咩慶祝嘢,一定要叫埋佢過去。」
「可能都係呢個原因,我哋可以維持到咁耐啦。」Lucas 說。
相伴逾 30 年,Lucas 笑言,生活已有如老夫老妻,多數時間在家裡吃飯、閒時打波、請朋友過來打牌,去外地旅行⋯⋯本打算就這樣繼續平靜愜意過日子。
電影《從今以後》去年上映,故事講述相伴半生的一對女同志,一方猝逝,未亡一方和對方親人處理身後事和遺產時發生矛盾。
Lucas 和伴侶看完電影,不無感觸。
「都⋯⋯都有少少諗下,都真係要諗下呢樣嘢喎⋯⋯」

Lucas 也從身邊朋友聽過不少,誰誰的伴侶逝世,但家人不接受二人關係;或誰誰年輕時被催婚,早與一名女子建立家庭⋯⋯都是一個個因時代造成的不幸故事。
「我都有聽過有啲圈入面嘅朋友,partner(伴侶)走咗之後,屋企人唔接受呢個 relationship(關係),啲嘢就全部被屋企人攞晒。」
「你無計㗎!法律上無得追究,你無權,完全無權㗎。」
年紀漸長,伴侶早幾年須入院動手術,Lucas 徹夜陪伴,當時醫生問他:你是病人的誰啊?
「你話我點答呢?我咪話兄弟、朋友囉。」
Lucas 承認,當時感尷尬,事後也懊惱自己為何不照直說。如今二人已完婚,「我而家唔怕醜㗎啦,我會照講囉。」他大笑。
「結婚係 go with the flow」
去年,碰巧團體「晚同牽」創始人江紹祺 Travis 問起他們,想不想參與同婚統籌公司舉辦的集體婚禮,兩人考慮一會兒,很快就答應。
「純粹就⋯⋯go with the flow(順其自然) 囉。」
沒有誰特地求婚,相伴大半生,名分與否,對他們而言分別不大。惟獨希望萬一誰病重、誰先行一步,婚書會有多一重保障。
所以 Lucas 相信,如果登記制度能夠通過,也是好事。
「我哋好早已寫好晒啲遺書,未結婚已經寫好。始終,如果我哋有啲物業,留返畀邊個,一定要寫好㗎嘛⋯⋯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一定要寫遺書啊。」

去年結婚後,二人也回過新加坡一次,擺酒和 Lucas 的家人朋友慶祝。
Lucas 有一侄仔侄女,兩人都是基督徒,婚宴前傳了一個訊息給他,大意說:「Uncle Lucas,我愛你,也恭喜你們,但我的宗教無法接受,所以我不會出席了。」
「我好開心他可以坦白同我講,」Lucas 說,「無所謂嘅,我尊重佢嘅 belief,我唔會逼你一定要出現。」
不過伴侶確有為此事感到傷心,「他都有話,我哋睇住佢大,他未出世我都已經喺度喇⋯⋯」
始終從較封閉的年代走來,有些謹慎至今未敢鬆懈,「好似喺公眾地方拖手,呢啲就唔會做啦⋯⋯始終個社會未到嗰個地步吖嘛⋯⋯」
不過 Lucas 近年頻頻公開受訪,他說年紀大了,別人喜歡說甚麼,開始覺得沒所謂。
「我就係我,我嘅生活,唔關你哋事,係咪?」他笑。
「其實我哋(同其他人)無咩大分別囉,即係兩個人,住埋一齊,都係一個家咋嘛。」
移工同志 / Jhovhie, Loi
「我們是 LGBT,是工人也是人」

Jhovhie 2009 年從菲律賓來港工作,至今已 16 年。
她記得小時候,當身邊女生都在玩 Barbie,她總是和哥哥及他一群男生朋友混,穿著 T 恤、短褲通處跑、跳橡皮繩。
但 Jhovhie 說,當年也沒意識自己是不是同志,因為那個年代的菲律賓,根本沒有人會談及 LGBTQ,「我只是隱隱覺得,自己跟其他人有一點不同。」
反而是身邊大人,見她總和男生們混,竊竊私語說她愛搞曖昧,大概是會早婚早孕的人。
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全國天主教徒佔人口八成。成長於八、九十年代, 她年幼時最深刻的記憶,是讀高中的時候,鄰居把他同性戀的兒子掛在樹上,一邊喊叫:「你要當直的!你要當個男兒!」一邊折磨他。
直至 18 歲那年,Jhovhie 已離家到工廠打工,認識了第一個女朋友,「當時我覺得這個 tomboy 很可愛,那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是 LGBT 社群的一分子。」
最後因對方另結新歡,關係只維持了一星期。不久後,Jhovhie 一位自小認識的朋友問她:「如果你要跟同性發展關係,為甚麼不選擇我呢?」對 Jhovhie 展開激烈的追求。
一年後,兩人走在一起,關係維持了 8 年,直至 Jhovhie 離開菲律賓到香港工作。
Jhovhie 說,當時她已跟這位女友同住,但 8 年來都不敢跟家人出櫃,除了因為是同性,也因為父親出身寒微,自小灌輸期望:女孩子要嫁個好人家,對方要學歷高,工作穩定。
有人問起對方是誰人,她都只會說:「這是我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
「我的家人也是很忠誠的天主教徒,在他們眼裡,人只有男孩、女孩、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如果你是 gay(男同志),你是 lesbian(女同志),你和其他人不同,你就是有罪之人。」
自由與束縛
Jhovhie 形容,離開菲律賓到香港工作,對不少 LGBT 移民工而言,在某些層面上,是獲得了一定的自由。
「我有些朋友,他 / 她們在菲律賓時已知道自己是 LGBTQ,但因為國內的情況、制度,他 / 她們很難出櫃。」
菲律賓法例對同性伴侶及性小眾的保障相當有限,社會風氣亦不算開放,「在這些情況下,你不是太容易可以自由表達自己。」
Jhovhie 到香港工作後交過好幾任女友,和以前不同,這些在香港結識的女朋友都有穩定工作,且她已離開家人在外地獨立生活,於是鼓起勇氣和家人出櫃。
「我第一個是告訴我的祖母,然後她竟然說,『好吧,沒有問題,只要你喜歡她⋯⋯她令你快樂,就可以了。」
告訴父親時,他的反應也僅僅是:「你問過祖母未有?她說可以嗎?那可以吧!」
「我也不知道為何她(祖母)可以這樣平靜,因為我童年時她很嚴格,是一個很虔誠的天主教徒,」Jhovhie 笑說,「可能對她而言,我們快樂比一切都重要吧。」
遠在他鄉,可在一個沒有人認識自己的地方再開始,Jhovhie 說,除此之外,在外地打工的收入比在菲律賓高,令本來在父權下被邊緣化的女性不僅財政獨立,甚至成為家庭的經濟支柱。
「當你負責賺錢、養活全家,這也是一個因素,當一些朋友要出櫃、說自己是 lesbian,他們(家人)很多時候就變得可以容忍(tolerate)。有些人可能慢慢會接受,但通常一開始也是容忍。」
「我已經獨立了,我花的是自己的錢,我不用依靠家人供養。當他們覺得你的錢是自己賺來的時候,你要出櫃就容易得多。」
「我在這裡結識的女朋友,我終於能夠如實跟家人講,她是我女朋友,她是我的伴侶。」

是同志,也是移工
不過,這種伴隨離鄉、財力提升的自由,只是硬幣的其中一面。
相約移工同志訪問過程一波三折。記者一開始透過移工團體聯繫有興趣受訪的朋友,本已相約在 8 月中一個星期天見面,未料受訪者連續兩個星期天無法放假,訪問只好一再延後。
在香港,法例規定外籍家庭傭工每年有 14 天法定假期(2026 年起增加至 15 天),工作滿一年後至少 7 天年假,以及每 7 天須有一天休息日。法例沒規定必須是星期天,哪一天休息由僱主指定。
根據政府標準僱傭合約,外傭須在僱主家中居住,不得外宿。全天候與僱主生活在一屋簷下,在同一空間工作與休息,不難想像,工作與私生活的界線變得非常模糊。
「我們有些朋友,他/她是 lesbian,想剪短頭髮,或穿得比較男性化,但在僱主家中會被禁止。」
同樣為女同志的的 Loi 說,也有同志朋友遇過,有僱主指控他 / 她對小孩子的眼神「有惡意(malicious)」。
「如果你在比較保守的家庭工作,你很難可以忠實表達自己。你要在他們面前飾演一個『一般』的直女。」
Jhovhie 也聽過,有僱主得知家傭是同志後,叫孩子不要再接近她,否則也會變成同志。
Jhovhie 其中一位前度女友的僱主非常嚴厲,不容許她在家中聊電話,故她們平日無法聯繫,只能於放假時見面。
「長工時也很影響我們的溝通。」Jhovhie 說,「但不僅是我們 LGBT 面對的問題,也是所有移工普遍面對的問題:容易遭受性暴力、長工時,沒有適切的休息空間、沒有足夠食物、低工資⋯⋯」
Jhovhie 和 Loi 能夠公開受訪,甚至組織移工行動,很大程度上仰賴現時的僱主較通情達理。
「我之前的僱主也知道,我告訴她我是同志,她說:『那你有空就帶女友上來吧,那我也可以帶女友上來了!』」
Loi 說,這也是為甚麼他們一直願意以真實面目示人,為 LGBTQ 以及更廣大的移工群體發聲。
「不是人人也有肯支持自己的僱主,我們非常幸運。」Loi 說,「如果我們也不發聲,就沒有人會替我們發聲。」

錯誤的時間,遇見對的人
愛情從來不只是愛情,本來就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密不可分。
政府現時提出的同性伴侶關係登記草案,登記條件之一為雙方或一方必須為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第 24 條,包括永久性及非永久性居民),另外亦規定登記的雙方,必須已於海外註冊同性伴侶關係,即婚姻或民事結合,才可於本港登記。
若條例獲通過,外傭要滿足為香港居民的條件未必有問題,但她們每月最低工資不足 5,000 元,要先去海外結婚,近乎天荒夜談。
「哪有錢?我們買新衣服也快要買不起了!」Loi 大笑。
Jhovhie 覺得,香港政府既然提出登記制度立法,「為何不一併容許在本地註冊呢?」
但她也認為,歸根究底若菲律賓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若移工長遠打算回國,「結婚也沒有甚麼意思。」
Jhovhie 現時的伴侶在菲律賓工作,兩人一起三年多,開始計劃將來。她希望再工作一段時間,儲夠錢,就回去菲律賓一起生活。
對移工同志而言,既礙於《入境條例》限制,即使在港居住滿 7 年都不能成為永久居民,同時因「十四天內離境」等僱傭政策,移工的命運跟著他 / 她的僱傭合約漂泊流動,如同不少人在暫居之地建立的感情一樣,難以確知終站。
Loi 說,有些人會修成正果,有些會無疾而終,更遑論部分人可能本來礙於種種社會壓力和期望,早在菲律賓有丈夫孩子,要維繫就更為艱難。
「有些人之後分隔異地,還可以繼續在一起;有些人會分手,但仍然是朋友。但只有很少人可以一起去其他國家(工作)。」
「其實這種感情真的很純粹,難以用言語形容。」
「有些人會問,我們這些關係是不是純粹為滿足情感?是不是只是尋找一些慰藉?但我相信這些關係、這些感情都是真實的。大家真的想去作出承諾,但你也可以說是⋯⋯可能有時候愛情就是發生在正確的地方,但在錯誤的時間吧。」Loi 苦笑。
文:梁凱澄
攝:COY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